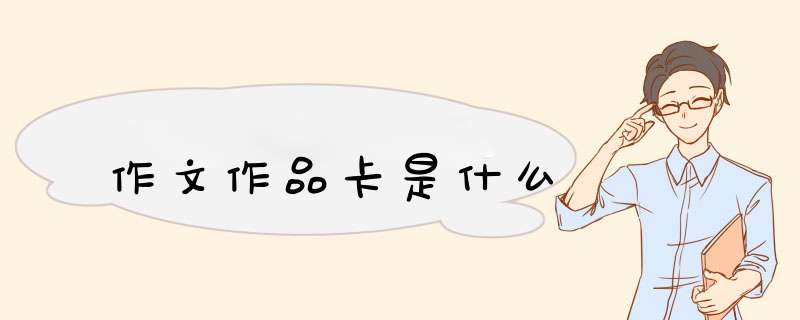
作品 泰戈尔诗集 描写人的短暂一生,如夏花你几年级?不然不能选书啊
七堇年新概念作文获奖作品?以《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一文入围初赛,以《在路上》一文获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被窝是青春的坟墓》 当我晚上听着安静得不得了的大提琴曲Paganini:Maurice gendrom,间隙之中听见十月的风在飞舞,以及南方秋天的夜晚里无比肃杀和凄戚的雨,手边的电话响起来,有着初中同学的问候,我温暖感动得不甘去接。
常常在这种时候有时光飞回流转的错觉,心疼得让峡谷内落泪。
在短短的国庆假期回到家,此刻躺在两年前曾经无比厌恶的这张床上。
我清晰地记得那些不眠又不醒的日子,像是一幅塞尚的油画,灰暗而斑斓,凌乱又优美,没有定义只有展示出来的伤口和甜蜜。
在经理了一个人的孤独生活之后,忽然感到自己以前对“离开”这个概念的误解有多么的盲目和荒谬。
那个对家庭有着深刻误解和怨恨的孩子,那些光线明明灭灭的回忆中的风景,以及这一去不复返的时光,都离我远去了。
我开始学着要去追悼她们,并试图为它们重新安葬一次,树一尊华丽的墓碑,以纪念我的一些失去。
在这个无比清冷的十月,我有看见我曾无比熟悉的,我家书房的天窗外的那块铅灰色天空,飘零的云朵,流泻的星辰,还有沉沉的黑夜。
我想起我事物岁守着它们走过来的路途,如此颠簸。
我知道我今天的妥协是建立在那些疼痛之上的,着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勇敢,青春期特有的不安:前者决定不顾一切地去不顾一切,后者决定不顾一切地去顾及一切。
我终有今天。
当我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忽然抬起头,感到头发被风吹乱并深深地掩埋了我的眼睛,单薄的衣服丝丝透着寒冷,笑容开始悲凉并且含蓄……我站在了一个预知的终点和另一个不预知的起点沙锅内。
疲惫的长跑永无终止,我们都是荆棘鸟,一生只停下来一次,那是死亡的时刻。
《青春无悔》里说,成长是憧憬与怀念的天平,当它倾斜得颓然倒下时,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该用怎样的声音去安慰。
——写在前面 一 很多很多个这样的晚上,晚春时节的夜晚里渐渐弥散开来的暗蓝色天光会随着很旧很旧的风迅速变浓。
我在灯光煞白的教室里看书和做题,抬起头来眼睛会因为疲劳而出现幻影,那种一条一条刺痛的影象,然后埋下头继续做,心里面什么也没有。
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每一天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记得刚进高中时,一个又高又漂亮的女孩儿对我说,被窝是青春的坟墓。
随后是她放肆的笑声。
这句话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脑海里一直没有忘记。
我已经离开家了。
着个学校一到周末,所有的孩子都提着大包小包回家,他们的父母殷勤地为他们敞开本田车的门,拎过包牵上车。
我收拾好东西回寝室,安静地生活着,安静到有风的下午,我站在运动场的看台上眺望黑色栏杆之外的郊区,瘦而好动的男孩,小饭店写着错别字的招牌,垃圾车轰轰地碾过去。
常常一直站到天色渐晚,天空中出现绝美的云霞,我才离去。
风却一直留在那里,厮守着有时候我疼痛的记忆惊惶挤出的一滴眼泪,花朵一样摇曳着。
有本书上说,寂寞就是你有话想说的时候没有人听,有人听的时候你无话可说。
2003年,在秋风恰至的时候我在无尽惶惑之中进高二,文科。
同桌是个很不简单的孩子,北木。
年级里很有名,看了许多书,把自己的文字打成漂亮的印刷体,大本大本地放在身边,有着天真的笑容。
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科生,非常勤奋向上我看着都感到害怕。
我一无所有了。
当我开始决定好好地找饭吃,我就放弃了所有的追逐。
牺牲了很多自由去换取另一个自由,最终得不偿失的后果让我不堪一击,我既写不出让老师们可以不吝啬分数给予的高考八股,又写不出我期待的表达柔软而精致的文字,最终庸庸碌碌淡淡然然悲悲戚戚地被以往,我看着它们,心疼如刀割,泪水久落不下。
北木是前卫少年杂志记者,有大叠大叠的乐评杂志和大摞大摞的CD,写大篇大篇的有意思的东西,看大本大本的哲学书比如那本不是人看的东西,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我觉得我一无所有,我买不起我看上的那件ONLY的上衣,买不到我想要找的电影《夜幕低垂》,我站在声色犬马火树银花宝马香车川流不息的大街上,在夜晚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看着店子橱窗里的一件很杰作的上衣,色泽沉静一如我过去的年年岁岁,裁剪异常精彩,我看着一千五百八十八的价码,望而却步的心情就像我初次面对感情时的胆怯。
我买不起,得不到,如此而已。
站在还有两天就满十七岁的无名悲哀上,我感到我涂抹着悲剧色彩的生命被阴影吞噬,就像一部分少年,惶惑,并一再怀疑。
我开始现实。
我看着 *** 场上那些高三的孩子因为不用穿校服而显得明媚张扬的样子,人人都是一张寂寞的脸。
我觉得说出“我高三了”这话一定非常骄傲,但我还没有。
我虽然已经安静地去一道一道地解数学,听课时用钢笔行楷记笔记,下晚自习后伴着常常没有月亮的夜色轻轻回寝室。
洗澡,上床,继续看书。
听一张大提琴,然后入睡。
生活得那样单纯,近乎局促刻板的平实具体。
听着楼下有女生拨吉他的声音我可以突然觉得难过,那把音色响亮的吉他躺在柜子里,清晰地记得换和弦时左手和指板摩擦而生的极似哭泣的声音,像是一种控诉。
妈妈周末打电话给我,要努力啊勤勤……我在电话这头用很温和的声音回答嗯我会的妈妈你放心。
大使抬起头就被穿堂而过的疾风刺倒,并看见我的青春这条路的尽头有黑色的洪流提前汹涌而来。
时光拉着我在这头迅速奔跑。
这条路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我非常难过。
北木有着许多最近一期的旅游杂志,捧着它笑容天真地说我想去哪里哪里,我觉得看这种说比自虐还可怕,北木也有同感。
我刚刚能够心如止水,死寂。
我不能像她那样桀骜地写东西,用漂亮的措辞非常优美地把中国的教育剐得体无完肤痛快淋漓,然后愉快地写下“我们单薄的青春……”最后是漂亮的批语和同样漂亮的分数。
我从小就只会写“李白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我看着这些空洞无边的东西已经非常平静了。
我的青春已经不再单薄,它已经厚重地踩多我抽身离开,剩下我紧紧拥抱着疼痛的理想。
当我周围的文科生们看佛经,把生僻的古文引到文章中显得语文功底不凡,把安妮宝贝的郭敬明的经典表达换个形式拷贝过来显得伤怀小资,还有那么多米兰?昆德拉卡夫卡海子杜拉斯村上春树包括那些作品像小王子彼得潘……这些原本美好的生命记录者和记录作品被一种虚荣和肤浅误读,我觉得很难过。
我宁愿只关心我的饭卡上还有多少余额,钱包里有几张票子还够不够我买张神州行来给SKY发短信。
就像我对北木说我太爱大提琴了我怕拉不好亵渎了它北木说你丫有自知之明。
因为我们都如此轻易地走到了别人的光环和阴影的笼罩下,愚蠢地聒噪,还坚信这就是自己的优点和价值所在。
而我淡然地坚持以苍白的语言尽我所能刻画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敌对,以及内心深处库存已久的冷漠与希望,决绝与妥协。
真实真实再真实。
青春,我可爱的青春。
北木写着长长的有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感性的探讨,把所能认识的哲思渗透进去,表达人文关怀,在晚自习的时候拿给我看,写得很好,是能得高分的作文。
我看了觉得难过也就是为自己难过。
因为一再告诉自己看现实,看高考,看成绩,看排名,其余山崩地裂世界末日与我无关没。
于是我曾有的澎湃的思想在不堪寂寞之中倏然消失,剩下一个空壳,一个渐渐瘪下去的球,滚不动了。
于一个孩子,这是很大的悲剧,一个真实的普通的悲剧。
个人的悲剧对历史不过是一行语焉不详的断句,时光白驹过隙,我们作为人类欲望这出壮阔的悲剧中没有野心的小人物,有理由对记录对由词语构成的历史产生怀疑,但是毕竟无能为力。
还记得2001年夏天,我在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叫做《天亮说晚安——曾经的碎片》的文字,我看了很多遍,那么的惊喜,像是呈于我的一个鲜活的梦境,靡靡繁华,难以名状。
我记住了那个叫四维的孩子,我甚至不清楚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可是两年之后,当他写书写得红得发紫的时候,《幻城》,《爱与痛的边缘》,《左手倒影,右手年华》……那些过分强调的单薄青春,那些泪流满面,那些明媚的忧伤……就像超过了文字所能承受的那样,泛滥成灾。
后来换个调调写的《一梦三四年》,《梦里花落知多少》……一切都远离了我印象中的那个优美,那个精致如同幻想一样的画面。
用卡付卡的话来说就是心灵的枯燥掩藏在感情洋溢的背后。
于是我觉得一切都有暗淡下来的那一刻,不管在绽放之初多像烟花般明媚绚丽。
年华年华。
二 在我屈指可数的几篇还算写完了的东西之中,我总是重复不断地提到十五岁那年的离别。
那是我心中完美的一道烙印,时时灼痛。
我记得以前张扬的日子。
蜷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一天一天地看云,且听风吟。
耳朵里塞着金属,或者你爱我我爱你的情歌,疯一样地写桌面文学,桌上墙上满是我的笔迹,为此赔了学校不少钱。
还有和朋友传纸条。
放学之后轧马路,十分钟可以回家的路途我要走半个小时。
那些昏黄的日日夜夜,我牵着靖的手走在日落的坡道上,与年轻的幻想相遇,询问快速流逝的光阴,心里无比平静地蔓延出忧伤,开满学校后面的山冈。
荒芜的风把我包围。
我知道我还没有到生命只剩下回忆的年龄,我一边恋恋不舍地回首,一边沾沾自喜地前瞻。
惟独冷漠地面对今日。
这是怎样的可悲。
回到家里困难着母亲疲倦烦躁却满是容忍的面容,心疼不已但是缄默。
我是她双手种出的麦子,我怎么忍心告诉她我是真的想离开了我真的不想再去学校了,我常常不做作业,我夜夜在锁了书房之后从来不会看书,我只是关掉灯,推开窗户,坐在七楼的窗台上一根一根地抽烟。
我常常深夜不想回家,因为无法忍受专断的家庭我宁愿选择自杀为反抗。
那个春天我在花园高大乔木下面待过很久,一地的眼泪。
城市里许多我十五年了都没有到过的小街小巷在那段日子被我一一踩过。
也曾经在最糟糕的夜晚放学不回家,我深爱的人把我揽在肩膀上无声哭泣,宁愿回家之后挨骂也不想走,我热爱这个黑暗中的城市,我坐在窗台上,凝望在我脚下匍匐行走的人们,疲倦而匆忙。
还有星辰一样的灯光绵延到黑暗深处。
天色渐晚。
在那些夜里,我总是觉得霞光内一个年轻的王,穿着华美的袍,站在悬崖上歌泣,脚下有众多的子民,都是自己的影子,天真的落寞的善良的罪恶的。
像是一场纸醉金迷的盛大演出,灵魂飘没。
可是我今天以晦涩的口吻把他们演示到纸上的时候,记录变得苍白物理。
那些花朵一样的过去,像时光一样无法库存。
四 当我趴在教室窗台上看着校园里归整划一的草坪和干干净净的水泥坝子,那些穿着校服背着大包包顶着纯色头发的孩子——那些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孩子踩着大步小步穿行的时候,我想起我小时候最爱坐上去的那堵围墙。
我坐在墙上一下午一下午地看秋风跑过山坡,叶子一夜间枯黄。
那时偷懒不练钢琴去山坡上和小朋友玩过家家,捡果子吃最终人赃并祸地被抓回来挨骂。
还有在舅舅的花园里把郁金香的球茎全部肢解,把汁液涂抹到衣服上。
我一时间竟然忘记了我已经不再年少,校园的喇叭里聒噪着小妹妹之辈写的酸里吧唧的抒情作文,黑板上还有一大片作业……我亲爱的不羁年华啊,小K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罚站的下午对着墙壁猜剪刀石头布,你突然说,“我要飞了!”于是我看见老师办公室的窗外掠过一群白鸽,静静的无声飞翔。
白色的羽毛纯洁得一如你挂着泥印和汗水的脸,干净得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觉得清晰如昨。
北木的文字已经凝练沉着得不需要再怕高考作文了,但是我呢?我已经不再关心心情之外的一切。
我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画家,重复地描绘同一处狭隘的风景。
风景消失了我也就该死了。
七岁那年在棍子的威逼下坐到钢琴凳上,画板前; 三年纪爱上文学看了许多名著虽然好多还是连环画; 四年级疯狂喜欢看漫画和画漫画; 五年级关心政治并立志做一名市长; 六年级有着坚定不移的女权主义信仰和家族荣耀感,热衷考古学的书籍; 初一时读了几本浅易的哲学书一时沉迷; 初二时喜欢心理学以及关于解梦,星相命理,塔罗牌; 初三时兴趣甚浓地热衷于初恋,夜不归家,沉默以及忧伤; 高一以蜕变的形式收归自我,乖张,并伴随轻度忧郁症; 现在的我关心天气,心情,事物,成绩。
唯一还会做的是翻开大卷大卷的素描,水粉画,速写,看看上面签的日期是否还完整。
然后找出五线谱一页页地翻,从拜厄到车尔尼599到749到849到299到740最后是前年夏天折磨死我的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5。
僵硬的手掀开琴盖,落到黑百键盘上,触目惊心地颤抖起来,像村上春树写的敏一样无法d下去。
抱着木吉他笨拙地拨了同一个和弦,一滴眼泪落下撞击在钢弦上我听见惊雷炸响的沉重控诉。
悲哀从心底溢出来,打湿我的脸,我沉郁下来,不再说话。
这就是成长吗,像是一页页翻书的感觉。
………… 我看着我自己。
心疼如刀割。
那个张扬的孩子哪里去了,本来可以不用这么快长大的。
我看着自己十六岁就开始衰老的头脑,悲愤,非常的悲愤。
我想揪住时光的衣领一拳打死他。
我感觉我身处蜂拥先前追赶幸福理想金钱洋房小车美女的趋之若骛的人群之中,夹在中间被踉踉跄跄地推着打着挤着撞着带向前去。
他们都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地在横流的物欲之中坚定向前追赶。
我不要。
我还遗忘了一个背包在后面,那里面装着我的玩具和事物。
我要回去拿……我一定要回去拿。
我会逆流而退的。
这是我的一个理想,我无数次梦见一个逆着人群行走的人,脸上刻着决绝与妥协并存的坚定与犹豫。
一直在行走,他的理想要么是找到世界的起点,要么毁灭在宇宙的尽头。
卡夫卡说,真的道路与其说是用来供人行走的,不如说是用来绊人的。
我在荒芜的风中迷惘地寻找星辰的方向,疲惫昂奋又停不下来。
创世之初的洪荒从神话和经书中涌来。
我站在岛中央急切地张望,可是天空之上的黑色飓风沉沉地压下来。
但是我依旧相信,我像耶和华一样仁慈地相信,我们作为有思维的生物是上帝的杰作,在黑色的天地之外有着明媚的雪原和祥和的村庄。
我们终将作为一个光荣的伤疤装点历史,然后被后人轻轻摩挲。
我们只是在经历一个生命的梦境,浑浊的相是处在绝路,但是在太阳醒来并开始将她的眼泪浇灌这片皲裂的土地之时,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就像那部戛纳电影的对白:“是的幻想,我们缺少幻想。
”我总是以抗拒的眼神看待荣枯迭替,昼夜轮回。
反反复复像是一首歌被翻唱翻唱再翻唱。
醒来,睡下,斗转星移。
我疯一样成天念着口头禅“我崩溃了”一边坏坏地笑,摸着北木的头说开光开光来我给你开光。
透过镜片可以看到北木清澈的眼神,神似一个可爱的顽童。
我看着觉得温暖。
我们过着单纯的生活,单纯得不用担心失业或者货币贬值,破产或者金融危机。
跑摸经济泛滥的后现代工业让我觉得其实太富了也不好,你看日本经济多疲软。
我们中国人举着红旗手捧着蛋在大道上浩浩荡荡的精神让西方人叹为观止。
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拥有着平凡的出生和注定平凡的死亡。
但是一路上由梦想,信念,抗争,忧伤以及不停息的鼓点,舞蹈大灶的青春,即使终将幻灭成灰烬飞扬之后沉沉落下,但毕竟不失华丽和悲壮过。
我在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青春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老去,又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长成。
回望起来,不止华衣与爱情,不止学习与时尚,不止鲜血和革命,不止奋斗和立夏功能,不止英雄与奉献。
”杰索鲁的“比马龙”效应告诉我们意志的确是生命不可缺少的力量。
在上个世纪海明威借用格特鲁德泰因的那句“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作为处女小说的开篇时,我们即被冷酷的岁月冠以了一个温暖如花开的名字“年轻人”。
所以我们高声呼喊年轻就是他妈一切的时候,不会有人指责我们的笑容太过玩世不恭。
青春的意义在于哪怕忧伤得泪流满面,依然是一首夹杂着摇滚味道的安魂曲。
五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发现窗外有着明媚的秋阳,灿若霓裳。
我想起在记忆深处飘荡的光斑,撒遍暗处的空白。
我像不听话的孩子那样,掀起还未开场的戏剧的帷幕,虔诚又调皮地窥视人生的悲喜。
那些隐藏在各式各样面孔背后的人们在赞美诗的废墟上演绎着他们豪迈的爱情与权谋。
在这种尝试性的描述中,我以畅快淋漓的恶意把人生撕碎了看,断章取义导致我一再错不可饶。
可是并不罪过。
因为对于从来都是完好地冷藏反抗性并循规蹈矩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人生还没有撕碎就已经死亡了。
契柯夫说,如果已经活过来的那段人生只是一个草稿,有一遍誊写该有多好。
可是我想,我潦草的青春和也许同样潦草的人生是优美的,没有成为物欲猎取的尤物。
北木的笔记本上有这么一段话: 原来有些事真的是不经意的完整,有些人真的是出乎想象的命中注定。
……无论上天给我怎样的去棵,我上演了十七年的悲欢,一些人一些事就这么明明灭灭地刻在沿途的风景中。
我学会了安稳学会了谎言学会了冷静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坚忍。
辗转中的快乐在百转千回中碎成一地琉璃,我站在风中把它们扫进心底最阴暗的角落。
再也没有关系。
那样明眸皓齿地对别人微笑,灵魂喷薄影子踯躅。
只剩坚强无处不在。
所以如果有不幸你要自己承担,安慰有时候捉襟见肘,自己不坚强也要打得坚强。
还没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举目无亲,我们没有资格难过,我们还能把快乐写得源远流长。
六 在物质丰富得不需要信仰来支撑的今天,我们有足够精力关心内心的小情调而不至于饿死。
这也是生活被关心感到空虚的原因。
我回忆起你的笑容在黄昏徐徐绽放,你的善良最终保护了我横冲直撞的爱情不至于遍体鳞伤,你一直一直都维护了我关于爱情的全部臆想没有聒噪坍塌。
还有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此宽容我与生俱来的冷漠和一些一开口就与寒冷相冻结的告白。
我怀着虔诚的感恩一路离别一路祈祷你们能在尘世找到幸福,虽然就像钱先生说的那样,永远快乐不仅渺茫得不能实现而且荒谬得不可能成立,可是因了祝福是对苦难的祭奠我们隐忍地活着就是甜蜜地对痛苦进行复仇。
所以我依然单纯地希望你们都永远快乐,愿我们把这句话以陪葬的身份带进坟墓。
我见过你最深情的面孔和最柔软的笑意,在炎凉的世态之中灯火一样给予我苟且的能力,边走边爱。
从前寂寞的汉字渴求海洋那样令人窒息的无尽关怀,但是在多年以后我们都看到了世界的荒芜和深不可测,即使被温暖如春的浮华与明媚所掩盖却依旧无法消失。
所以我总是对朋友们说要好好地过,好好地过。
成长必然充斥了生命的创痛,我们还可以肩并肩寻找幸福就已足够。
你,秋秋,昊,紫倩,小冷,桃子,虹,靖。
我想纪念你们。
在我十六岁垂垂老去之前的朋友。
我知道你们对我的爱以各种方式表达给我,也许我曾经拒绝收到,可是在我回忆往事的时候这一切熠熠生辉,炫目得我来不及遮住眼睛就淆然泪下。
一路的聚聚散散中我们曾经围在一起取暖,风雨无惧。
虽然在冬天过去我们又将收拾好各自记忆的行李匆匆上路,走在这弥漫这广阔忧郁的土地上,一如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候鸟一样的年轻人一样,很快就各奔天涯。
可是风景依然是存在的,我们都见过梦里的如黛青山,满溪桃花,野花迎风飘摆好象是在倾诉衷肠,绿草萋萋抖动恰似相恋缠绵……似水年华,如梦光阴,此生足矣。
每个星光坠落的夜晚,我裹紧棉被沉沉地闭上眼睛。
浅浅的睡眠,如梦的梦幻,醒来,你已在彼岸。
《在路上》 看清这个世界,然后爱它。
——罗曼·罗兰 我提起笔在柔软的纸上书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感到前所未有的由疏离而生的想念。
我永远都记得我的第一篇文字,它叫”被窝是青春的坟墓”。
已经过去了很久的事了。
对我说这句话的那个又高又漂亮的女孩子已经休了学准备去澳洲了。
她现在在天天练习高尔夫球,听说很厉害,一场下来只比职业选手多打了十杆。
偶尔她会回学校来看看旧同学,人缘甚好地被围个里三层外三层,最近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是上晚自习之前,麦色的皮肤,高挑而迷人。
是那种天生就很有魅力的女孩子。
我远远地和她打招呼,没有走近。
毕竟谁都不会记得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在军训的大营百无聊赖地玩过的游戏。
和一些小得不能清晰记起的愉快往事。
可是我怎么无法忘记她对我说的,被窝是青青的坟墓,以及她那个时候肆意绽放的年轻笑靥。
虽然这么快这些人就在你的世界中远去,并预备不再重现。
但还是会很想念。
这些都是最真诚的想法。
弥足珍贵。
我翻开看以前写的文字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轻浅地笑起来,里面矫饰而玄虚的表达显得稚嫩无比,虽然我明白我现在亦是如此。
可是它于我的意义,像一个城市被围困了十七年。
它在其中血脉贲张地疯长,最终抵达逃逸的边缘。
有个被这一代的学生作者用烂了的词叫物是人非。
其实真的是这样。
我们躺看,唱着,年复一年,时代在我们身后舞蹈着飞奔,而我们蜷在灵魂的围城里面坐井观天。
这真是形象,比如我明白我将满十八岁并坐进五楼高三的教室里受刑的时候,我心中这样悲哀地清楚,像爱默生说的那样,因为要每个人住在自己的家里,所以这样的世界广大无比。
但我想也许我终其一生无法触及它的一隅。
我觉得我再也写不出那么多堆积的词藻了,这几年的高中时代跌跌撞撞地爬进来,人都觉得疲倦。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张床我就愿意倒下,管它兵荒马乱地从我身上碾过去。
深夜倒在床上,突然想不起到底有没有刷牙,一直想一直想,想到自己没有力气想了,就睡着了。
甩开CD的耳机,懒得去按OFF键。
听见声音在夜色里盘旋。
感到时光迢迢而去。
淡入淡出。
离我第一篇文字,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日子。
转眼到了一个毕业的季节,学长们在考完试后的日子常常回到学校来。
我喜欢他们生动的表情,带着欣欣向荣的自由的味道。
我从他们的笑容中间穿过,直上五楼。
那是最安静最棒的教室,从高大的窗子望出去是南方湿润的天空,或者夜晚疏朗的星辰,这都是献给这个寂寞的高三的礼物,在这寂寞得年复一年的年少岁月里。
高二的暑假我看了最后一部电影,是巴尔纳多·贝托鲁奇的《梦想家》,电影里是巴黎的一九六八。
一九六八的少年。
我不知道一个中年人会拍出这么充满年少激情的电影。
我相信这些都是不能被提起的往事,否则他们会不可遏制地熊熊燃烧在已经干瘪躯体里。
学生运动,五月风暴,文化大革命,布达格之春。
世界的一九六八是疯的,是少年的。
如今我从镜头里远远地看着那个遥远的时代,一直在怀疑它的真实性。
高三之前最难过的事情,是童走了。
我记得那天她在教室收拾东西,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可是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发现桌子上有一只袋子。
打开来,里面是岩井俊二、斯坦利库布里克、安东尼奥尼和安东尼·明格拉的四部电影,还有一张字条,就是小七我走了。
DVD要好好保存喔。
我眼泪一下子就落了。
一点预兆都没有,童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拿着字条,想起这些影碟是我很久很久之前开玩笑时拜托她买的,她就这样念念不忘。
我心里难过得要死。
后来问另外一个她很好的朋友,才知道她已去了英国。
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
这个不爱说话的总是一个人快快行走的孩子,这个在这两年多里对我最好的孩子,这个走遍城市给我找我想要的电影的孩子,这个善良的孩子。
再也不会有了。
我想起她走之前一直找我要照片,我还一直闹着不给,还有她缠着我要我写我家的地址我也不写,心里狠狠地疼起来。
是不是一定要收到一封贴着外国邮票并写满英文的信我才懂得记忆和珍惜。
我一回头看到那个空荡荡的座位,想起这个孩子的单纯和善良心中就无限寂寞。
童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孩子,在现在这个时候,像她这样的孩子已经很少很少了。
而我们甚没有真正道别。
余下全文可参见 七堇年百度贴吧,或你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我想要第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获奖作品选中的一篇文章《海盗远航》书法习作和书法艺术作品有什么区别?书法习作和作品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练习,一个是正式的。
有的时候练习的作品也很不错,可以当作正式的作品去装裱、参加比赛。
但是他还需要整理,所以我们把平时练习的作品拿出来和正式的作品对比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书法习作就是相当一部分在临帖,也有集字创作,也有基本的创作,但是他是一个练习的过程。
可是艺术创作是要进行文字和整体的构思要,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
首先,目的不一样,练习好比演员演出前的排练,是解决基本书写技巧、提升筆墨表现力,提高对书法的认识的一种手段,其过程中能解决一些局部问题,而创作好比演员经过大量排练后上台演出,其要求更高、更全面,个人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创作是一个即兴发挥的过程,其结果不仅与书写者的个人的基本功、天份、文化艺术素养有关,还与书写者的身心状态、外部环境、工具材料的状况密切相关,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曾经提到这一点: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