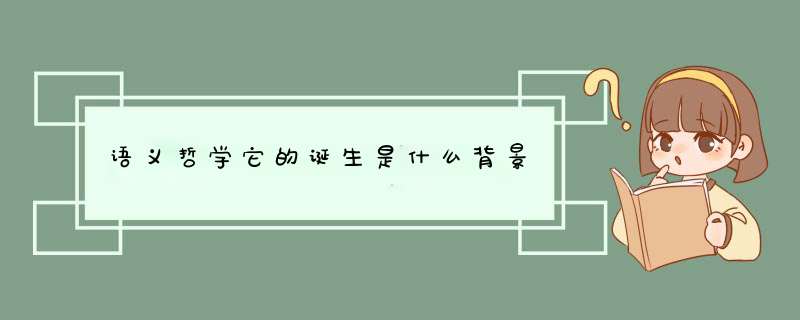
毫无疑问,语言不仅是人类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工具也是科学和哲学应该研究的一个对象,但语义哲学(包括罗素之后的逻辑实证论)却因此断定:语言不仅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对象而且是唯一研究的对象。语义哲学认为,确定语言是哲学的唯一研究对象就可以取消关于“实在的问题”,消解传统哲学因“本体论”而带来的“语义分歧”,并逻辑地推出“思维与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语义哲学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的主观经验论传统有着历史的内在联系,而主观经验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贝克莱与休谟,他们的哲学是语义哲学的重要的思想来源。我们的下面的分析,就是依据这样的历史线索展开的。
要详细说明语义哲学的历史渊源,就必须从贝克莱和休谟谈起。尽管这些在哲学上属于常识,但为了说明问题的实质,就不能不从这些常识性的问题谈起。
(1).乔治.贝克莱(1684——1753)
贝克莱1684年出生于爱尔兰,1700年开始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和任教。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视觉新论》(1709)、《人类知识原理》(1710)和《希勒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1713)。在完成《对话》后,他离开了三一学院赴美洲从事传教活动,希望在英国的殖民地百慕大群岛创办一所大学,以“改进”美洲的文明。1728年之后,在英国国会的资助下,他两次赴美洲企望实现创办大学的希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734年,他回到了爱尔兰,任克罗因教区的主教。
从贝克莱的生涯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为哲学而哲学”的人,哲学对他来说是论证神学和为神学服务的工具。指出这一点是要说明,贝克莱为什么会以唯我论和“上帝”作为自己哲学的归宿。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经验的解释有两种基本类型:客观经验论和主观经验论。客观经验论的代表是柏拉图和黑格尔,他们承认客观实在的存在,认为客观经验在本质上是思想的存在或者是“普遍一般理念”的存在,例如对于桌子,我们不考虑它是木头制作的还是石头制作的,也不考虑它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这些都是客观的桌子而不是桌子的“理念”,桌子的本质是舍去桌子的这些客观表象后抽象的桌子的“理念”,也就是桌子的基本构造所表示的桌子的“普遍形式”。主观经验论认为所谓的客观实在只是心灵的一种构造,而经验就是来自心灵构造的主观感受(所谓的“内在经验”),同样是桌子,主观经验论认为桌子的存在不是因为桌子的客观属性,而是因为“我”看到了桌子的颜色,摸到了它的形状,闻到了桌子的油漆气味。
在西方哲学史上,贝克莱被公认为是主观经验论的创始人。在贝克莱看来,既然有观念就必然有感知观念的主体,而观念的主体就是自我,因为观念不能存在于感知它们的人心之外。例如说有香味,只是说我闻到过它;说有声音,只是说我听见过它。贝克莱的主观经验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心外无物。在贝克莱看来,从天上的星宿到地上各种不同的事物,它们的存在就是“我”所感知或被“我”感知,任何独立于主观经验之外的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是“荒谬”的。因此,贝克莱断言:“存在(esse)就是被感知(percipi)”。
在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中所要论证的就是“物体就是观念的集合”或“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这是主观经验论的哲学基础,也是后来的主观经验论哲学从贝克莱那里继承的主要东西。
按照贝克莱的说法,世界万物都不过是“我”的感觉,都存在于“我”心中,被“我”感觉而存在;那么,在“我”的感觉之前,以至于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又是怎样存在的呢?如果一切事物只有被“我”感觉时才能存在,那“我”一闭上眼睛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就都是子虚乌有的了,只要“我”一睁开眼睛就又被创造出来了吗?为了摆脱这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贝克莱自相矛盾地用客观经验论来为自己辩解,他振振有辞地声称:“虽然我们的确主张,感官的对象不是别的,只是观念,而这些观念不能不被感知而存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它们除了只被我们感知外,就不能存在;因为虽然我们没有感知它们,但是还可以有某个别的精神感知它们。当我说物体离开心灵就不能存在时,……我所指的乃是一切心灵。”在这里,贝克莱偷换了经验论的概念:把主观经验论偷换为了客观经验论。贝克莱竟然忘记了自己哲学前提:除了“我”的感觉之外,不可能有“他”(包括上帝)的感觉的存在。
贝克莱所谓的“一切心灵”已经脱离了哲学范畴变成了一个神学范畴,也就是“上帝”的代名词:“我”所感觉的一切来自“一切心灵”,而世界就是“一切心灵”的创造,造物主的存在形式就是万能的“上帝”。
贝克莱哲学中主观经验论的不彻底性,引起了休谟的不满。于是,休谟在修补和改造贝克莱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更彻底、更精致的主观经验论哲学。
(2).大卫.休谟(1711——1776)
休谟1711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曾经学过法律,并从事过商业活动。1734年,休谟第一次到法国,在法国他开始研究哲学,并从事著述活动。1763年,休谟又去法国,担任英国驻法国使馆的秘书,代理过公使。1752年至1761年,休谟曾进行过英国史的编撰工作。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1740)、《人类理解研究》(1748)、《道德原则研究》(1752)和《宗教的自然史》(1757)等。
休谟和贝克莱一样,也不是一个“为哲学而哲学”的人,他与贝克莱不同的是一生的主要经历不在宗教方面而在社会政治方面,其学术生涯与自身的社会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
休谟做为贝克莱主观经验论的继承者,同样主张人的“知觉”是知识的唯一对象,他的哲学也是从分析感觉或知觉开始的。休谟认为,人心中的知觉有两种:一种叫“印象”,另一种叫“思想或观念”。所谓印象,就是较强烈、较活跃的知觉。用他在《人类理解研究》中的话来说,就是人在“有所听,有所见,有所触,有所爱,有所憎,有所欲,有所意时的知觉”。所谓“思想或观念”,则是比较弱的、模糊的印象,是印象的“摹本”。按照休谟的说法,印象和思想都是观念,但这两种概念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的思想虽然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它可以把我们过去的印象(感觉或情感)按照实在的样子摹拟出来,但是——休谟说:“思想所用的颜色是微弱的,暗淡的,还不及我们的原来知觉所有的颜色……诗中的描绘纵然很辉煌,它们也不能把自然的物质绘画得使我们把这种描写当做真实的景致……最活跃的思想比最钝暗的感觉也是较为逊弱的。” 在休谟看来,思想或观念所反映的不是客观经验世界,而是印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这些印象的混合和配列的集合。观念摹拟印象,印象产生观念,思想可以没有被反映物从“观念摹拟印象”中产生,这就是休谟主观经验论的前提。
那么,什么是印象,它是怎样产生的呢?休谟认为,感觉“最初是由于一种未知的原因产生在心中的”。至于这个原因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我们是找不出任何论证来证明其原因的。他因此断言,除了我们的感觉之外,我们“再也不能设想任何一种存在”。既然外部世界是不可知的,那么,人们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呈现在自己心中的感觉和印象,“永远不会真正超越出自身一步”。因此,在休谟看来,所谓“存在物不是别的,只是心中的一些知觉”。当我们说,一张桌子、一棵树、一所房子的时候,所指的不过是人心中的知觉。到了这里,休谟不过是在重复贝克莱“物体是感觉的组合”这一命题,已经没有丝毫的新意。休谟与贝克莱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排除了贝克莱哲学中唯我论的因素,用不可知论取而代之。休谟清楚地看到,唯我论是贝克莱哲学的必然归宿,而哲学真正达到唯我论境界时就意味着哲学的自我消灭:任何人的主观经验、宗教信仰都是哲学,因此“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适合“人人”的有普遍意义的哲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休谟为了摆脱贝克莱唯我论困境,提出了哲学上的“第三条路线”,他宣布:除了感觉以外,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上帝的存在也和客观世界的存在一样是没有根据的。这样,休谟就认为自己“成功”地摆脱了唯我论,把感觉之外是否存在什么东西的问题“取消”了。休谟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温和的怀疑主义”,也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不可知论”。
当休谟是从知觉、感觉出发宣布一切存在物都不过是“各种不同知觉的集群”时,并没有摆脱主观经验论的限制。他所谓的哲学上的“第三条路线”不过是用回避问题的方式来回答问题,用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问题并没有因为休谟的主观臆断而消失。相反,休谟所例举的瞎子不能构成颜色的观念,聋子不能构成声音的观念,正好证明了人的感觉经验如果脱离了客观实在就无法产生的真理。
休谟在否认客观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客观存在的规律性。按照休谟的看法,客观经验世界规律,例如因果规律,并不是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只是在人的思想中或想象中的“一种习惯性的联系”。休谟认为,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现象经常前后相继,有一种现象出现便会有另一种现象发生,所以在人的思想中便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联系,认为两钟现象是必然联系着的;因此,一种现象再发生,人就料到另一种现象也就必然会再出现,并断定后一种现象是由前一种现象所导致的。休谟认为,这只是人的错觉,人所能够知道的只是两个现象的同时并存或前后相随,而在自然中暗藏着的那些“奇妙的力量”或“神秘的能力”,是永远也不会被人所认识的。休谟说:“我们能发现各种事情相继出现……可我们永远看不到它们中间有任何纽带。”例如,第一个子d的运动冲击第二个子d后,便出现第二个子d的运动;但是,不能因此推断:前者是后者的原因,而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因为两个子d的运动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在第一个子d的运动中发现任何结果来。因此,这两个子d的运动只是“会合”在一块的,而不是“联系”在一块的。他甚至说“太阳明天要出来”和“太阳明天不出来”这两种断言都是可以成立的,等等。
休谟反因果律的“论证”,所采用的是混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手法,把现象等同于本质或者说“现象就是本质”。就拿子d的运动来说,人所看到的仅仅是子d运动的现象,而子d运动的规律则是在q械中受到撞针的冲击后由d壳的内部火药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而产生的力学运动,这是任何子d运动都遵循的规律,完全符合牛顿力学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定律,因此有着因果必然性;而子d与子d之间的关系则完全受开q人的偶然性的控制,与子d运动的必然性没有联系,所遵循的是子d在射击过程中与目标之间的概率统计规律——只有在统计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子d“集合”的意义。“太阳明天要出来”和“太阳明天不出来”这两种断言,是直接与人的日常经验相悖的,因为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是受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和自转的规律支配的,如果古典天体力学的定律是正确的,那么太阳“太阳明天要出来”和“太阳明天不出来”这两种断言,只有一个是真的,另一个必定是假的;因为,按照天体力学所揭示的天体的运动规律,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和自转决定了太阳每天“升起”和“落下”的断言是必然的、也是唯一的。
休谟很明白,他的主观经验论的因果观不仅与科学相矛盾,而且也和人的生活常识相违背。如果人只知道自己的感觉却不能认识客观规律,那么人到底依靠什么行动呢?对此,休谟诡称,人的行动是靠自己的“习惯”或“信念”,而这种信念不是来自知识而是来自“信仰”。休谟对“习惯”所下的定义是:“习惯就是人生的最大指导”;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人的存在,但我们却“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休谟“人靠什么行动”的观点的话,那就是如同流行歌所唱的那样:人是“跟着感觉走,让梦牵着手”的!
关于休谟,就说到这里为止。这里之所以要考察贝克莱和休谟的哲学,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是西方20世纪语义哲学的发源地,语义哲学在继承贝克莱和休谟的哲学衣钵的基础上又给主观经验论披了“逻辑实证”的现代数理逻辑的外衣。
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被公认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领袖石里克在语义哲学的期刊《认识》杂志第一期中,发表了题为《哲学的转折点》的社论,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在这篇社论中石里克说:“那么,什么是哲学呢?呃,哲学不是一门科学,但是,它却是非常重要而且伟大的东西,因而甚至现在我们还能够把它看作科学的皇后,虽然它本身不是一门科学。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规定过,科学的皇后必须本身是一门科学。今天我们认为哲学不是一个关于认识的种种结果的体系,而是一个关于种种活动的体系(system of acts),这就是当代哲学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是一种活动(activity),通过这种活动我们断定或说明陈述的意义。哲学说明语句,而科学断定语句。”不难看出,石里克宣言的本质,就是把哲学从理性反思的高度降低到了“说明语句”的非理性的“解释学”的水平上。
在同一期刊里还有卡尔纳普的《旧的和新的逻辑》一文,他在文中附和石里克宣言说:“这个期刊从本期开始所表明的新趋势,是从事于支持一种新的科学的哲学思维方法,这个方法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描述为对经验科学的定理和概念的一种逻辑分析……”卡尔纳普与其他逻辑实证论的追随者一样,在执行石里克的纲领方面是前后一贯的。在石里克宣言公布几年后,卡尔纳普在《语言的逻辑语形》中写道:“哲学应当为关于科学的逻辑所取代,那就是说,应当为对于各门科学的概念和语句的逻辑分析所替代,因为关于科学的逻辑不是别的,而是科学语言的逻辑语形学。”卡尔纳普对石里克宣言所加的注解是:哲学就是“逻辑语形学”。
上面之所以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贝克莱和休谟哲学思想,是因为可以通过贝克莱和休谟的哲学看到语义哲学的理论发源地,并看到哲学上的所谓“第三条路线”在语义哲学中是如何历史地逻辑地走到了自己最极端最激进的顶点,并在唯我论中完成了哲学上的自我消灭,变成了真正的“定义学”和“解释学”。我们可以看出:石里克所谓的“哲学的转折点”,不过是休谟的“不可知论”的20世纪版本,是主观经验论登峰造极的哲学表现。
语义哲学是在沿袭了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经验论基础上,把哲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了“语言问题”,从而把人的世界限制于语言,限制于那种作为人的内心经验的外部表现的语言实体(entity)。这种形式的主观经验论导致了唯我论,而维特根斯坦则用明确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唯我论。
主观经验论,自从它采取内在哲学的形式把经验解释成为来自心灵“影象”的内在经验的时候起,就以和主观唯我论哲学紧密联系的姿态出现。20世纪的语义哲学不仅包括是贝克莱和休谟衣钵的继承者,也包括马赫那样的“经验批判论者”,而逻辑实证论与经验批判论有着直接的联系。马赫主义者认为印象在哲学上是中性的,印象的主观性或客观性是根据原则同格(koordinationsreihe)来决定的(阿芬那留斯)。语义哲学的创始人及其代表人物对语义哲学起源所作的回顾(主要刊登在《维也纳学派》杂志上),都证明了这种哲学与马赫哲学的联系。
对语义哲学起源的历史分析表明:20世纪的西方哲学在反叛客观经验论的过程中,选择了主观经验论来重新建构西方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不过是在抛弃以客观经验论为基础的理性传统的基础上,继承了贝克莱和休谟主观经验论的非理性传统,因此并没有象某些人声称的那样是“反传统”的产物。那么,西方现代的语义哲学是以什么方式继承和发展了贝克莱和休谟主观经验论哲学呢?
西方现代语义哲学是以数理逻辑为工具的。数理逻辑作为一种“符号逻辑”与“语言符号”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本体论”的问题似乎“消失”了或者“改变了问题的提问方式”。语义哲学所谓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不过是休谟的“除了感觉以外,一切都是不可知的”观点的20世纪版本。逻辑本身在语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看来,是“独立于主观经验与客观经验之外的中性的”东西,而数理逻辑的作为“符号逻辑”与语言有着完全的一致性,所以“语言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逻辑和语言一样:“逻辑的界限也是世界的界限”。因此,在语义哲学看来,现象和本质是没有区别的,现象就是本质,世界就是语言所涵盖着的“图象”的“集合”,而每一个“图象”都是“逻辑命题”——超越“图象”的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没有意义”的世界,不能被“图象”所表示的事物就是“不能被理解和认识的事物”,也就是“没有意义的事物”。
语义哲学在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号下,却宣扬着最形而上学的东西。逻辑本身是客观经验还是主观经验的产物?数理逻辑作为“符号逻辑”命题演算的规则所遵循的是客观经验还是主观经验?数理逻辑的符号是“图象”还是“图象”所反映的内容?语言所指称的对象就是语言本身吗?当我们说“太阳”或者“Sun”的时候,是有着具体的指称对象的,如果脱离了指称对象是“发光发热”的恒星实体,“太阳”或者“Sun”作为指称符号就没有任何意义。但语义哲学却认为,事物只有在赋予它“符号”后才是有意义的“能够经验把握的”,如果没有“指称符号”(语言)那么指称对象就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我们“经验世界”以外的没有意义的东西。
语义哲学把数理逻辑绝对化和无对化的实质就在于,逻辑在哲学的意义上被形而上学化了,而语义哲学本身也就建立在了主观经验论的“逻辑本体论”的基础上,从而逻辑地走向了彻底的唯我论,完成了哲学上的自我消灭。语义“哲学”作为哲学没有任何意义,作为工具则是人人都可以使用的:数理逻辑作为推理论证的工具适用于经验科学,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哲学,对于其他哲学来说逻辑只有方法的意义,方法是论证对象的手段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此,数理逻辑在语义哲学那里,不过是唯我论的、人人适用的工具,它只能依靠其他哲学发挥工具的作用,本身已经失去了哲学意义。
罗素对语义哲学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它把语言看成是哲学唯一的研究对象。这种批评是有充分的根据的,语义哲学关于原始语句的(protocol sentence)的理论(就是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还原成原始的语句,并认为主体的某些基本经验和印象中的原始东西是认识的唯一内容,知识的大厦就建筑在这些东西上),确实是主观经验论的一种新的激进的形式。如果说,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歪曲和谋杀的话,那么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也是对罗素哲学的歪曲和谋杀。因此,对语义哲学的批判,必须从对维特根斯坦的批判开始。
三
维特根斯坦主观经验论唯我论的哲学思想,集中在他的逻辑专著《逻辑哲学论》中。这部著作所代表的是要消灭一切形而上学的语义哲学流派的哲学主张,但事实上它却是柏格森直觉主义及其形而上学的混合物。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他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语义哲学的基本观念:语言是哲学唯一研究的对象,哲学的任务被缩小到解释科学语言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在《逻辑哲学论》发表许多年后,卡尔纳普在他的著作《语言的逻辑语形》中,确认了语义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并表示他同意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思想,除了维特根斯坦下面这两点之外:不可能表述出那些关于语形的语句,不可能表述出那些关于科学的逻辑语句。那么,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述的,到底是些什么思想呢?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写道:
“5.5561 经验的实在受到客体的总和的限制。这种限制也在基本命题的总和中出现。
5.6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5.61 逻辑充满了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
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思考,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的表述,并没有达到语义学所要求的“消除语义分歧”的要求,而是含混不清的:“经验”、“语言”、“逻辑”在他那里都充满了柏格森直觉主义的神秘色彩。维特根斯坦的“经验的实在”在受到“客体的总和的限制”的条件下,也相应地受到了“基本命题的总和”的限制;他的“经验实在”并不是意识之外的客观经验的实在,而是受到“基本命题”限制的“经验实在”,也就是主观经验(内在经验)的实在,这种“经验实在”的实质是“现象就是本质”,“现象”是人的主观意识对现象的“基本命题”,因此“经验实在”就是“基本命题”的总和。正是在这样的主观经验论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才“推导”出了唯我论的哲学结论:“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也就是说“经验实在的总和”就是语言所能够表述的一切,“语言的界限”之外的东西则是“我们不能思考的东西”——也就是所谓“我们不能说”的东西,而“语言的界限”是和“逻辑的界限”等价的命题。
维特根斯坦为了消除人们对他的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陈述(“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所的解释的质疑,在《逻辑哲学论》中进一步说明了对唯我论的看法:
“5.62 这句话对唯我论在什么程度内是真理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实际上唯我论所指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它不能够说出来,而只能表达出来。
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个事实,表明于:语言(我所理解的唯一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5.621 世界和生活是一致的。
5.63 我就是我的世界(小世界)。
5.64 这里我们看到了严格贯彻的唯我论是与纯粹的实在论一致的。唯我论的‘自我’缩小至无延展的点,而实在仍然与它相合。
5.641 因此,真正有一种在哲学上可以谈论的‘自我’的意义。
‘自我’之出现于哲学中是由于‘世界是我的世界’。
哲学上的自我不是人,而是人体或者心理学上所说的人的灵魂,而形而上学的主体,是界限——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虽然维特根斯坦声称:“一切能够被表达的东西,都能够被清楚地表达出来。”但在他上述的“命题”中,却以晦涩的方式引入了最形而上学的对象,而且这些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世界的元素而是世界的界限。当维特根斯坦声称“实际上唯我论所指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它不能够说出来,而只能表达出来”的时候,很神秘地把“表达”和“说”作了区别,能够“表达”而不能够“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因为维特根斯坦接下来要“论证”所谓的“哲学上的自我不是人”,而是“人体或者心理学上所说的人的灵魂”。那么“灵魂”的“图象”是什么呢?作为一个“逻辑命题”的指称对象又是什么呢?当“自我”以“灵魂”为归宿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就彻底暴露出了自己哲学的本质:“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而语言主体的“自我”则是“灵魂”,所以说到底世界的界限就是“灵魂”的界限,而“灵魂”界限内的世界和宗教世界有什么区别呢?维特根斯坦所宣扬不仅仅是赤裸裸的形而上学,而且还宣扬着赤裸裸的造神者的谎言!由哲学的唯我论走向非哲学的宗教神学,维特根斯坦因此完成了哲学上彻底的自我消灭。
维特根斯坦在继承罗素的的关于基本命题的理论的时候,并把这个理论不加限制地推广到语言学的时候,到达了语言上的唯我论。这种唯我论的主要意义包括在下面这个语句中:“我的语言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界限”。维特根斯坦从这个表述所导出的种种结论,在语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首先,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地说明(逻辑地分析)思想的任务交给了哲学;在他的心目中,逻辑地说明思想就是一种“关于语言的批评”;
其次,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地说明思想还原到语言的语形方面,使思想完全同语义方面脱离开来;
第三,他认为一切超越“语言界限”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因而是一个“假问题”。
关于维特根斯坦,就说到这里。最后,引用罗素在《对意义和真理的研究》中对语义哲学的批判来结束本文:
“当我说‘太阳在照耀’,我并不是表示,这是若干相互之间没有矛盾的命题中的一个;我是表示某种不属于语言的东西,并且也正是为了这个原故就创造了象‘太阳’和‘照耀’这样一些语词。语词的目的是处理语词以外的事物的,哲学家好象把这个简单的事实都忘记了。如果我走进一家饭馆点菜叫饭,我并不是想使我的话同其他的话在一个系统中互不矛盾,而是想促使食物的出现。我可以不说话而通过自己去拿我所需要的东西这个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不过这不及说话方便而已。某些现代哲学家的语言理论,却忘记了日常语言的这个通常的实际的目的,而使自己迷失在新-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中,我似乎听到他们说‘一开始就是语词’,而不是‘一开始就是语词所表示的东西’。在这个试图成为极端经验主义的努力中,竟会出现这种回复到古代形而上学的情形,这是值得注意的。”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