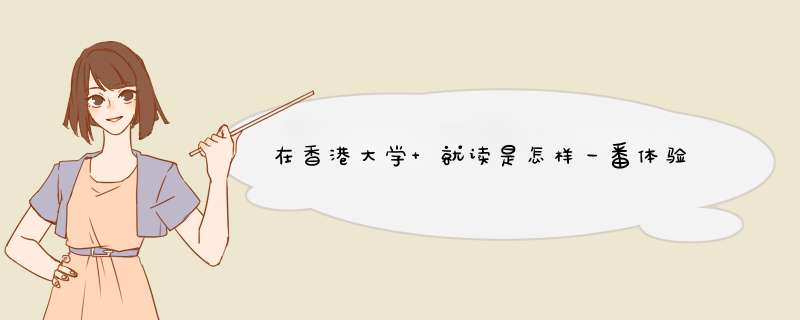
在港大读书的辰光,我都住在圣庄(St John's College)。这个舍堂,课外活动是很吓人的,半夜里绕岛跑啦,没日没夜的唱楼歌啦,当然就不读书了。还好,不强迫我参加的。我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听门外惊天动地的声音。翻几页陈寅恪先生的书,又看看窗外的山坡。偶尔还能看见松鼠的。但眼睛一眨,它们已经被楼里的“喊杀声”吓走了。
在房间里固然可以把书看下去,但要上厕所的时候,就会有问题。经常,他们在楼道中间开楼会,把通往楼梯和洗手间的路都堵死了。有一趟,憋了好久,终于忍不住了。我看着一个上海的同学在主持会议,就悄悄走过去。他已经和本港的学生打成一片了,是一个小头头的样子。我望着他,也不好打断的。他余光扫了我一眼,小手那么一挥,集会的人群就已经自动分成两波,空出一条小小的通道,让我跻身过去。
很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港大生活大概就浓缩在这样的场景中了。这里有很多我不能适应的东西,但这里也有更重要的东西。她是开放的:她欢迎所有的人来参加,如果你真的投入,他们甚至欢迎你来做“摩西”。但同时,她还能够容忍:能容忍我这样奇怪的人,让我做一些自己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开放与容忍并存,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港大——开放让这个地方繁荣,但容忍让她变得伟大。
但或许,那只是从前的港大了。是为序。
2
圣庄离学校不算很近。沿着薄扶林道,上上下下的,走个十五分钟才到图书馆。走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蒸发了。可以掏出八达通,去卖饮料的地方“滴”一下,就有一罐很冰的喝喝。那时候,我们喝很冰很冰的。
图书馆一进门的地方,是New Addition,就是我们说的新到图书。那时我经常想的是萨特的一个人物,叫“自学者”,他从书架上最左边一本开始读,一本本读下去,觉得有一天就可以读完天下的书了。我胃口小一点:如果把新到图书一本本读完,那至少某年以后的图书,我就都读过了。实际上,我也就读那些序和跋,读那里的悲与欢。常常,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有的人结婚了,有的人有了孩子,有的人父母老了。那些,仿佛都是和我有关的事情了。
心情好些以后,我就会去二楼,AV Reserve Collection。并不是看成人视频的地方。这是说有声的(Audio)和影像的(Video)。所以偶尔和朋友一起看个老电影什么的,文艺一把。那年刚引进了一批很舒服的沙发垫。经常就团在那里,像猫一样团起来,继续想那些有的没的的事情。有一趟,我的一朋友一脸绝望地和我说过:“大人,我也中招了。” 我一愣。回想起来,这个词用得真是贴切。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只是利用他,他都是知道的,就是不能自拔。那些日子我们都陷在那里,很深的垫子里。团起来,取暖——图书馆的空调真是太冷了。
离开AV不远的,是哲学书。架上的并不多。即使是西文图书,也比北大的少。很快就可以把法国哲学的都摸过一遍。累了,就坐下来,像自己家一样。这里,庶几没有人来的。只有一回,来了一个姑娘。我就问她:“你找什么呀?”她竟然回答我了:“德里达”——仿佛是在讲,“你还不退散呀。”顺手,我就从“我”的书架上抄起了几本书,“喏,Of Grammatology、Writing and Difference,就在这里了。法语的,或者其他的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我屋有本Marges de la philosophie,你要的话我借你……”
好吧,从前我就是这么爱炫技的……我真的错了。
3
到点了,就要去上课。内容通常都很简单的,尤其在人文学院。香港的学生,很少会来选择来文学院。并不是香港人不厉害。他们中,但凡有志于文史的,很多已经在英美或北大了。还有许多或许会选择中文大学这样的地方。港大在本地人印象中就更加偏法学、医科还有商科。
英文系以外,语言学系是港大人文学院最受欢迎的专业,毕竟对于以后工作可以有些帮助。我上过一门课叫Languages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Typology(世界的语言:类型学导论),老师随口问了一句,“十九世纪语言学在做什么呀?”我也随口说了,“历史比较呀。”他很吃惊的,立马就问:“你怎么知道的!”我不假思索地讲:“在复旦每个人都知道的……”在场就震惊了。在这样会心一击的时刻,当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张松大人的头像。
其实,在香港的每一天,我都很想回到复旦。我在那里委托培养一年。那是我的家。但我本来是那里的。彼时,复旦每年卖一点生源让港大挑,换一点别的好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被挑中了。然而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港大。我问了来招生的老师,“老师,你们有没有古典学系呀?”她说,“嗯,好问题呀。我们港大的院系设置是参照牛津剑桥的。”这回答真是太巧妙了。港大确实是参照牛剑的,只是不包括古典学系而已。
4
平日里,常常溺在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里,就觉得很对不起港大的老师们。他们真的太好了。
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听说了我录取的故事,就义务教我们古希腊文。每个周二和周四,一大早,她都提前一个小时来教室,给我们开小灶。她是意大利人,她上的小学希腊文是必修,所以教法就很“传统”。我们不讲名词变格,也不讲动词变位。有半学期都在讲连音变化……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只是很努力地争取记住。
其实,额外地加课真是很寻常的。有时,两点到四点的课,结束了,我们还愿意听,老师就继续讲,讲到六点以后,带我们去吃饭。一边还问我们许多生活与读书的事情。那些时候,养成了我见到老师就很紧张的性格:总感觉我的琐碎的存在,于他们而言,真是一种污染的。
我很弱的,英语也不好。老师们就手把手教,文章一个字一个字改。我有次交了一篇哲学习作,然后那个老师就把我叫过去了。他是个美国人,长得很像画中的酒神。他说,“你这文章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希望用他的方式批评他。但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不清楚。”所以,他就帮我一句句讲,第一句,“你的这句话可能有三个意思,一、二、三……” 2000字的文章讲完,密密麻麻的都是他的标记,原先的字都看不清了。从此以后,我听到“清楚”(clarity)这个词的时候,都不能不紧张起来——酒神要批评我了……
许多时候,老师们就像家人一样的。那时我们的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他把我推荐给剑桥的一个老师了,对方已经同意了。后来又有一次说起,我很没出息地说,“那很贵吧。”老师竟然说:“会困难么?我可以借给你,随便什么时候还都好。”不知道那样的时刻,时间是怎么过去的。那些时候,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是僭越与冒犯的——又觉得自己甚至连这样想都是不可以的,这想法本身意味着自己仿佛是什么——这也是僭越了。这些万般的感触,直到今天还在心里游走。只是处处都披上了深秋的颜色:那是无边的愧疚。
5
从办公室出来以后,还是可以有许多趣味的。
有一天我同学神神叨叨地问我:“你知道CCP是什么?”我想了想,“应该是Chinese Communist Party(某国某党)吧?”他说,“对的,那CCCP呢?”“苏联……嗯。”这我知道的。“那你知道SSSP是什么吗?”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这个……”我想想……“难道是South Senegal Slavery Party(南塞内加尔亚奴隶党)?”“不对啦,是Stanley Smith Swimming Pool!”这是我们这里的游泳池。蓝蓝的天,蓝蓝的水,热热的风,凉凉的茶。仿佛可以忘记许多的烦恼。
从游泳池可以沿着很陡的街道往下走,就可以遇到老式的有轨电车。据说,这里原来是个红灯区,那时的人下了班,逛好了窑子,是要回家的,就开通了一条公交线。有个学者说,中世纪大学和妓院的起源其实也差不多。都是因为有了城市,很多年轻的人背井离乡没人管,或者读点书,或者卖点身,其实都是讨个生活。说来,香港当年也是这样的。现在,有轨电车已经换了地铁了吧。
往上走,就可以行山。经过张爱玲以前住的房子,再走一个钟头不到,就到太平山顶了。那其实是个旅游胜地,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湾,当然也有很多小店。有次许多人一起上山,一个新闻系的同学说她很喜欢这里的商场,还有香港的每个商场。我就笑了。香港哪有很多商场的,只有一个商场,叫香港。显然,后来,她就不和我说话了。其实我也喜欢这些小店的。手头宽裕的时候,就可以买一壶酒,看一看夜里的城。远远的水面上,是斑斑点点的光影。热风吹来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想起韩愈啦、李德裕之类的,想想他们在南国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
“应该回去看书了呀!” 这时,就该启程回圣庄了。
可以蜷缩在并不很小的房间里。有一地的书。少喝点水。早晨会有很好吃的火腿炒蛋。又要跋涉去图书馆了。我们要去了呀。去到或远或近的地方。
我知道的。圣庄曾经走出了很多很好的学者。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一个本港的学长就带我们参观了远近的古迹。后来他去了北大,现在,他是当下最好的青年西夏学学者之一。其实,这些年里,我渐渐地明白了:也许,那些舍堂的活动也不如想象中可怕,香港也并非是全然学术的荒漠的。毕竟,还有那些许多许多的心绪,荒芜了太多本该读书的辰光。再不振作起来,那,就是真的荒漠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