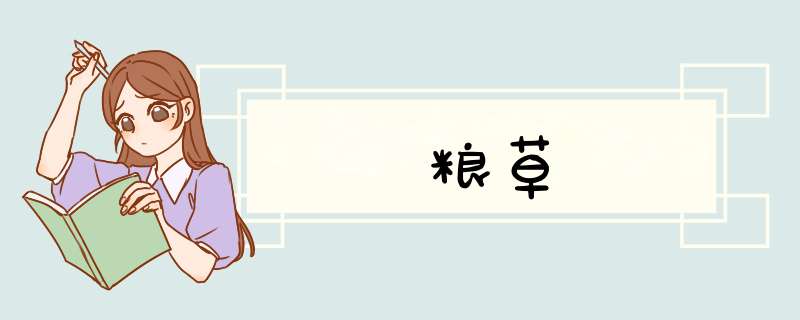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赢得一场战争,必须要有所向披靡的军队,更要有粮草补给。
粮草最初是指军队运输的衣服、铠甲、人和马的食物、军械、棉被等物资,后来这个词语开始被广泛应用。
粮草中的食物,行军带着的多为一些干粮,比如小麦和小米,这些粮食容易保存,且能当主食。
行军打仗是不能经常吃到蔬菜的,受国力和运输条件影响,顺利的话,能吃饱饭,如果不顺利,被敌人断了粮草,或者国家无力支付军用开支,那么连饭都吃不上。
如果行军顺利,将士们是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的,由于蔬菜不容易保存,所以他们只能在行军途中购买。
宋朝之前没有炒菜这个说法,他们吃饭只有三种方式,那就是蒸、煮和烤。
那个时候,讲究点的人还会吃个没辣椒的火锅驱寒感觉美美哒,因为辣椒明朝时期才传入中国。
他们吃饭,一般是架起几口大陶锅,然后煮粥,煮完里面放点盐,全军将士吃的美滋滋,这是粮草充足的状态,粮草被切断几天不吃饭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
当然,军队里的领导和功臣是偶尔能吃顿肉,喝点酒的,普通士兵连闻都闻不到,他们就等着打胜仗后皇上能犒赏三军,让他们吃顿饱饭!
中国古代军人到底吃什么,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让我们按照时间线来捋一捋。
先来看春秋战国,《诗经·大雅·公刘》中有这样一段诗:「笃公刘,匪居匪康。
廼埸廼疆,廼积廼仓;廼裹餱粮,于橐于囊」。
这里所说的“餱”,是把蒸好的饭曝晒成干饭,装在行囊里,用作行军打仗的干粮。
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行军干粮的记录。
春秋时期主要的粮食品种是黍(黄米)和粟(小米),因此这个“餱”应当是蒸熟晒干的黄米饭或小米饭。
黍的生长期比较短,能耐高寒,但口感和产量都不如粟,因此能种粟的地方就很少种黍。
菽(大豆)也是先秦时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但由于种植大豆的需水量是粟的三倍,大豆在战国时期灌溉技术发达后才进入主粮的范围。
《战国策》里提到的“豆饭藿羹”,即煮熟的大豆和用豆叶做的羹汤,就是土壤贫瘠的韩国常见的百姓食物。
由于直接把大豆煮成豆饭吃会导致腹中胀气,连续放屁,因此贵族通常并不吃豆饭,而是将其加盐发酵,做成豉、酱来食用。
至于稻米,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属于珍贵的食品,孔子曾问宰我,居丧的时候「食乎稻,衣乎锦,于汝安乎?」可见孔子时期吃稻米在北方是被视为和穿锦衣一样的高级享受在出土的居延汉简文献中,可以看到汉代戍边军人领取军粮的一些规定,以及粮食出入和库存的记录账簿,比如「 最凡粟二千五百九十石七斗二升少,凡出千八百五十七石三斗一升,今余粟七百卅三石四斗一升少,校见粟得七百五十四石二斗」「有余亖十二斛。
万岁尽第十吏卒三十亖人,凡五十亖人,人六斛,用谷三百二十斛」「今余粟七百卅三石四斗一升少,校见粟得七百五十四石二斗」「出糜小石十一石六斗,九月戊辰朔戊辰通泽」「糜五斛一斗,正月十一日中舍子通取」…… 可见西汉时,北方军粮以谷、粟和糜为主。
顺便说一下居延汉简中记录的物价:粟百钱一石;谷、黍、糜子一百五十钱一石;小麦九十钱一石;(猪)肉每斤四至七文钱, 肝每斤四五十钱,胃和肾每斤三四钱,肠每斤二三十钱, 脂(动物油)每斤六钱,鱼每条一钱半至三钱,鸡每只三十六钱,菜狗每只一二百钱, 小羊每只二百五十钱,大羊每只九百钱; 醇酒五十钱一斗,行酒十钱一斗; 盐四百钱一石。
日常用品方面,布每匹三百到五百钱,帛每匹三百三十钱,絮每斤十钱,皂布衣三百九十钱,单衣一百钱,布绔三百钱,韦绔六百钱,袍一千一百到一千九百钱。
六尺长的席子一百三十五钱一条。
铁剑价格是八百钱一口, 马每匹四千到一万钱,胡狗(军犬)六百钱一只;壮牛九千钱一头,老牛三千钱一头, 拉货的牛车一辆二千钱;普通田地九万钱(九十贯)一顷,关中长陵附近肥沃的灌田二十万钱一顷……西汉居延汉简记录的军粮多为谷、粟,而清朝学者王心敬总结历代军粮制度,称汉代兵粮之法是“八麦二米”,这应当是北方小麦种植面积扩大之后的事情。
注重,这里的米并不是稻米,而是多指粟米和黍米。
汉朝虽然有征南越、闽越等战役,但更主要的用兵方向还是北方。
当时中国北部地区种稻的面积极少,最常见的作物仍然是粟,而居第二位的是小麦。
先秦时代中原地区虽然也有麦子,但是吃法是整粒煮食,而且产量也不高。
秦汉时期解决了制约小麦成为主粮的两大关键问题——灌溉和磨粉,董仲舒就曾上书汉武帝,要求推广小麦的种植。
小麦无论是整粒保存还是磨粉保存,储存期都比较长,而且还可以烤成胡饼(烧饼、馕)一类的食物,让士兵随身携带,因此成为兵粮的主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清代王心敬在《饷兵兼用麦米说》一文中认为「麦米皆养人之物,而北人食麦,视米味为美;其性则视米性为足,增气而健力,故北方人无一日不食饼。
即陕省坐镇之兵,每领来官米,亦往往粜钱市饼而食也。
」明清时期,中国北方诸省的粮食作物仍以麦子为主,“种麦三倍于种谷”,所以有“三秋不敌一夏”的谚语(麦子在夏天收获,明清时所征的赋税叫夏税;稻米在秋天收获,相关赋税叫秋粮)。
整粒的小麦如果不入水淘洗的话,可久贮数年。
无论是整粒炒煮食用,或者磨粉制作面饼,或者制作炒面,都很方便。
古代军队在行军打仗的间隙扎营支帐,割草喂马,挖掘水井。
埋锅造饭一般是在天明以及日未落时(古人多一天吃两餐),比如永乐八年明成祖率军北征蒙古,就严令日出之前以及日落之后禁止生火做饭。
在不具备做饭条件的地方,就要用干粮来充饥了。
还是以明成祖这次北征为例,「各军沿途炒面……每军关与小麦三斗」。
编纂于明代的《养生类要》一书中记录的“炒面方歌”配方是「二两白盐四两姜,五斤炒面二茴香」,如果要追求更香的味道,还可以「半斤杏仁和面炒」。
当然了,行军打仗携带的炒面不可能如此精细,一般是用小麦、大麦、青稞等作物磨粉加盐,在铁锅内用木耙子炒至黄熟,然后就可以装袋备用了。
吃的时候要加水搅成面糊糊,如果直接抓吃的话,吃几口就会被噎住。
比如清代的《钦定兰州纪略》就说“……断水三日,虽有炒面作粮,亦不能下咽”。
除了炒面之外如果还能吃到肉菜,对士兵来说是莫大的伙食改善。
明成祖征北时,曾经下令把光禄寺和尚膳监为皇帝携带的米面、腊味、枣子等食品分赐给军士(酒、砂糖、盐、酱、胡椒之类则不予发放),此外军中携带的牛羊,以及从蒙古人手里缴获的牛羊牲口,也都宰杀“将作粮食,接济军士”。
宋代兵书《武经总要》中,记录了行军打仗对食物的大致需求量。
每人携带干粮三斗,可以驰战数旬。
干粮的制法是取米一石,净淘炊熟,晒干,然后再蒸再晒,如此反复十次,得到二斗干粮。
食用时每次取一合(十分之一升),先用熟水(开水)浸泡,等湿透了以后煮食之。
此外《武经总要》里记录了几种便携式调味品的制法:盐三升,放入锅中,加水,用炭火徐徐熬干,结成盐卤。
可供一个人食用五十日,在湿热多雨的夏日携带也很方便;豆豉三升,捣成膏状,加盐五升,捻作饼子,晒干。
每顿食用枣核大的一块,可以代替酱菜;小麦面做成蒸饼(馒头)一枚,取一升醋,反复浸入、晒干,至醋尽为止。
每顿取梧桐子大小的一粒;粗布一尺,用浓醋一升浸泡,晒干,再浸再晒,至醋尽为止。
食时剪下一寸布放入水里煮。
如果班师在道,去境尤远,储贮乏绝,可捡择羸瘦牛马宰杀食用。
牛一头、马一匹可供五十人食用一日,驴一头可供三十人食用一日;松树皮十斤与米五合同煮至极烂熟,半斤可供一人食用一日;每人带油麻子半升,如果缺水的话取三十粒含在嘴里,可以止渴。
乌梅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到了明代,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面曾记录了一则行军干粮的做法:米二升,炒黄,一升研为细末,一升另包;麦二升炒熟,一升用熟香油作媒,一升取六合,用好烧酒浸晒干,再浸,以不入为度,研末另包;四合用盐醋晒浸,亦以不入为度,晒研为末,另包。
把这四升炒米和炒面包裹到一起,是供一人食用的分量,包裹外面书写本人姓名。
行军之际,除非被敌人围困至紧,或者粮食未能运到,否则不许擅自开启食用。
如果出征时忘记携带干粮包,与遗忘兵器同罪。
从制作方法中能看出来,炒米是作为主粮来食用的,而炒面用香油、烧酒、盐、醋调味,用于改进口粮的味道。
戚继光的另一项发明,也流传至今,就是福建特产“光饼”。
乾隆时期出兵台湾平定林爽文起义时,就曾让闽浙总督调集绫绸、布匹、灰面、炒面、光饼、药料、牛骡,作为大将福康安征台的军用物资。
今天的光饼成为地方名吃,馅料很豪华,有猪肉葱花、肥肉霉干菜、虾肉、香菇、紫菜、花生碎、黑糖等多种选择,也有把白面光饼掰开夹上火腿肠、午餐肉甚至鸡排的吃法。
但明清时制作光饼的原料很简单,就是将面粉稍微发酵,也可以加上一点点食盐,洒上一点点芝麻,烤制而成,这个和美军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主粮,“烤制硬面包”非常相似。
相传嘉靖四十二年倭寇侵犯福建,戚继光领兵入闽剿倭,连日阴雨无法造饭,于是烤制面饼让士兵随身携带,由于只是干面饼,因此烤好后放上三五天也不会变质。
闽北百姓依法仿制,犒劳戚家军。
为方便士兵携带,光饼中间有个洞,可以用绳子串起挂在身上。
“棋子”也是古代常见的一种供军旅和行人随身携带的干粮,比如明代的《西游记补》三十六回中有「我等是行路的客人,身边儿带着些干粮棋子,过这有名的饿鬼林,却被林中妖魔抢去」。
这里所说的“棋子”是一种用面粉和水做成的食品,捏成围棋子的形状,形圆而小,如同糕点、馒头。
既可以煮吃,也可以炒吃。
为了改善口味,可以在和面时加入盐、生姜汁、胡椒,甚或动物油脂、煮肉汁等等来调味。
北宋开封市井中有“细物料棋子馄饨店”、“肉齑淘棋子”、“素棋子”,南宋杭州有“三鲜棋子、虾棋子、虾鱼棋子、丝鸡棋子、七宝棋子”。
清代入关之前的《满文老档》中,也有攻城间隙让士兵休息吃炒面的记录,努尔哈赤赏赐萨哈廉夫妇的物品有「各色果子,及盛炒面荷包二,染色水獭皮二」,可见后金入关前炒面之普及,以致出现了专门的“盛炒面荷包”。
康熙、雍正朝连年对准噶尔用兵,当时配给士兵的口粮是每人每日支粟米八合三勺、或炒面一斤。
平时陕甘兵士每个人都要随身准备十五斤炒面,一旦紧急征调出发,这就是半个月的口粮。
雍正帝认为这个口粮数额在平日驻扎时本无不足,但遇有事之际,昼则追奔攻击,夜则防范巡查,“恐旧数稍有不敷”,于是下令改为每人每天粟米一升、或炒面一斤四两。
在进军青海时,班禅额尔得尼和颇罗鼐贝勒还遣人向清军赠送酥油、炒面、牛、羊、干粮。
乾隆年间,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
当时从内地征调至准噶尔前线的满、蒙、索伦、巴尔虎、喀尔喀、厄鲁特等族士兵,要随身携带足够食用四个月的炒米、炒面、干牛羊肉等干粮,抵达新疆军营安扎后,如果没有战斗任务,每人每月支给二十日份的食米(一斗六升六合),以及羊一只、盐菜银一两五钱。
乾隆十九年时,让陕甘总督筹备军粮,以六个月计算,应准备粳米一万一千二百余石、炒面二百二十五万斤、白面七十五万斤、羊二万只。
跟役、余丁等非战斗人员准备口粮数为粟米六千七百石、炒面及青稞面一百万斤、白面四十万斤、羊七千八百只。
此外还要支取全军六个月的“盐菜银”十七万九千六百两。
每石炒面的成本是银一两五钱三分。
由于炒面分量较轻,每头骆驼可以驮载三石炒面,还可以夹带缎匹、鞋靴等物资。
负责驮运军粮的是山西的“皇商”,每头骆驼向官方收取脚银九两八钱。
清代文献中记载的行军所携干粮,主食类有粳米、粟米、青稞面、白面、炒面、棋子、光饼等等;副食和调料有乳油、酥油、茶叶、盐;肉食有牛羊肉干、活羊、活牛,但是没有携带活猪的,一是猪不如牛羊驯服,不易牵赶(成语“狼奔豕突”就是很形象的例子),一是猪的饲料不如牛羊方便省事。
当然,清代许多领兵的大帅,比如年羹尧、福康安之流,是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著称的。
比如年羹尧从大将军贬为杭州防御后,其侍妾星散,有杭州某秀才得到一女,昔日是在年羹尧帐下管饮馔的,专门负责做小炒肉一味菜。
秀才请她如法炮制一道小炒肉,这位女仆哂笑说:“年将军做一盘小炒肉,需用一头肥猪,只不过取其最精华之一块罢了。
如今你家买肉只买几斤,叫人从何下手?!”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