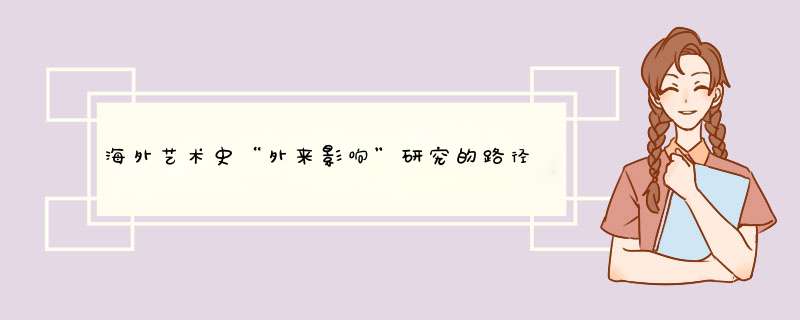
文 / 宋石磊
内容摘要:海外艺术史研究已然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近百年来海外艺术史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演变发展,对于中国艺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海外艺术史“外来影响”研究切入,探究从20世纪初到当下影响至深的美国艺术史学界东、西部学派之间的分歧,梳理其各自研究路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差异。尤其是高居翰所呈现的艺术史研究新面貌与艺术史的另一种可能,无疑对于当下中国艺术史研究亟需的路径选择及其可能性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与启示。
关键词:海外艺术史 “外来影响” 路径 方法
引言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已然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涌现了大量的艺术史研究著作。但相对于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等学科而言,国内对海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仍缺乏全面的认识。从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来说,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者所带来的“他者”的文化眼光,无疑为国内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一种“跨文化”研究的视野。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之下,国内艺术史学界加快了对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翻译工作,迎来了国内艺术史译介的第一个鼎盛时期。〔1〕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机构相继出版了海外艺术史系列丛书,这对于快速建构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具有重要价值。但这也引发了学界对于海外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薛永年的《美国研究中国画史方法述略》较早地从“方法论”的视角对美国研究中国画史的方法做了反思性概述。林梅村的《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调查之一》从考古学的视野对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研究方法做了述评。朱其的《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概述》对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论争、流派、思潮
生成与发展的来龙去脉做了综述性介绍。汪燕翎的《幽闭之鹤——十年来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境遇》对十年间海外中国美术研究学科转型的新旧交织、身份混杂的现象做了阐释,旨在借“他者”来反观中国艺术史学科的自身境遇问题。另外,对于艺术史属于美术史还是艺术学理论领域这一问题,国内学界一直颇有争议,王一川在《艺术史的可能性及其路径》一文中回顾了中国艺术史学科建构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被质疑的悬而未决的艺术史急需探索其可能性及路径。如何使海外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创造性转化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本土路径和范式?因此,有必要对海外艺术史研究的路径、方法及问题做一个全面梳理,本文从笔者近年来所关注的海外艺术史的“外来影响”〔2〕这一颇具争议的学术前沿问题切入,以点带面,管窥美国艺术史学界东、西部学派之间的分歧,梳理其各自研究路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差异。希冀对当下中国艺术史亟需的路径选择和方法论提供一定借鉴。
一
关于中国艺术风格的“外来影响”研究,是海外艺术史进行中国艺术研究叙述的一个重要观念。学界历来争议颇多。日本学者米泽嘉圃(Yonezawa Yoshiho)试图寻找西洋绘画影响的可能。〔3〕其立足点在于晚明画风变革与西洋绘画存有必然关联。在1970年,台北故宫的国际中国古画讨论会上,苏立文与高居翰最早提出晚明中国画家所受到西洋画中的图像、观念与风格的影响。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考据了晚明耶稣会士所传入中国的图画为何以及中国人如何得见这些图画。〔4〕高居翰(James Cahill)运用风格学形式分析的方法,通过欧洲铜版画对比17世纪晚明绘画不同画家及作品风格,指出西洋绘画是推动17世纪晚明绘画发展变革的关键性因素,由此激发了17世纪晚明绘画中的原创活力,并进一步举证阐释晚明的一些画家诸如吴彬与张宏等人如何地运用了这些西洋绘画技法。〔5〕班宗华在《董其昌与西法——向高居翰致敬的一个假设》一文中也探讨了中国艺术的“外来影响”研究问题。他旨在探讨董其昌的《婉娈草堂图》所出现的新颖的结构和质感形体的全新艺术风格之灵感来源,通过对交叉排线光影法与欧洲蚀刻铜版画的基本技法比对,他进而指出这种营造光影的技术与强烈的三维立体团块造型绝不是传统中国画的特征,联系1597年董其昌的人生经历与交游圈,这种新颖手法来源于耶稣会士利玛窦所带来的西洋绘画。〔6〕这一推断显然是建立在高居翰的“董其昌乃是经由耶稣会传教士之接触而为他所见到的欧洲艺术所影响”〔7〕的观念之上的。
从艺术史的脉络来看,高居翰的学术理路带来了另一种路径及可能性,“外来影响”研究在高居翰的笔下呈现一种新面貌。高居翰并非传统海外艺术史研究的“冲击—反应”模式,而是持本土传统与西方外来刺激双重影响的立场。所谓“跨文化借用”的说法,即暗示用一个文化强制另一个文化的观念,其实是值得商榷的。这显然是无法阐释晚明绘画“新颖”技法所出现的复杂成因的。高居翰由此坚持认为晚明绘画受到了西方绘画“外来影响”的刺激,从而激发了传统内部新的质素。
很显然,高居翰受到巴克森德尔(M.Baxandall)的影响,摆脱了之前由一系列含混的议论组成全过程的风格研究范式,转而致力于研究社会与历史条件中的艺术。〔8〕因此,高居翰深入晚明的多重艺术史原初文化历史语境之中考察,进一步指出风格的革新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明清易代之际,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思想变动之中,虽然西方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未至,但是却给整个思想文化界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激发了本土传统内部新的质素,使得明清画家得以重新审视自身传统。高居翰研究范式的创新意义在于,在海外艺术史中国艺术研究的“普遍性”观念与晚期绘画“衰落论”之外,指出了晚明绘画革新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高居翰并非持一种“外来影响”的绝对论,而是将“外来影响”作为一种刺激,试图重新审视晚明绘画本土传统内部的原创活力。晚明画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新处境,北宋自然主义的写实已然发展至极致,加之明清遗民画家的两难处境,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寻求西方绘画之“外来影响”的刺激并加以“创造性转化”本土传统,从而带来了晚明绘画革新的可能。正如高居翰所下断论:“在经历了登峰造极的北宋时期之后,中止了五世纪之久,才又复兴;而北宋风格在此时复兴,我相信乃是由于中国人突然的接触到西洋画中类似的特征,因而受到了刺激……其来源必得自于西洋构图。”〔9〕
高居翰在沿用风格分析和图像研究方法之时,又打破了风格研究太强调“分期”,以及总体风格的概括,缺乏一个对应关系的模式的弱点,转而以一种遗民“生活方式与风格倾向”(life patterns and stylistic directions)的对应关系来对艺术作品的绘画风格进行形式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解读艺术形式背后的遗民心态与文化想象。即晚明遗民画家吸收西方外来刺激的影响,正是鉴于东西方艺术在观察写生与再现自然方面的相似性,西洋风景画与北宋时期的山水画作在反映自然实景方面有着某种相似性,而西方外来刺激强烈的“明暗对照法”更易于传达遗民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失序的状态。因此通过西方绘画“外来影响”的刺激来促进理想的山川与理想政治秩序的北宋巨障山水的复兴,希冀恢复社会政治人伦“道统”的秩序,从内部绘画形式与外部社会语境两方面表现理想的山峰,晚明绘画的革新的重要表现便是北宋巨障山水的复兴。
高居翰的“外来影响”研究的理论来源是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的风格学与形式分析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探讨“时代风格”与“风格的连续性”二者之间关联,即管窥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风格共相”。“一旦研究者试图要在横向的各种表现形式之中,或者是在纵向的时间轴上,探究一个普遍或一贯的风格共相,那么他必然要面对何以有此共相的问题”〔10〕。高居翰在前人基础之上,提出中国绘画史研究必须以视觉方法为中心。〔11〕在《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一书中,高居翰将北宋巨障山水的复兴作为17世纪的最重要且最具艺术史价值和意义的艺术事件。并进一步指出:“大约是从1610年以降,有一批山水画家,其中包括业余画家和职业画家,出身于北方的省份及福建——这两个地区都离长江下游的画坛重镇甚远——重新发现了北宋风格的伟大之处,并且尝试重新加以捕捉,使其入画。”“这批画家活跃于南京,另外则有很少数是在北京,而当时想要求见并观摩北宗画收藏者,也尽在这两处。”〔12〕而关于这一艺术史事件的解读,高居翰坚持晚明绘画的新颖手法的粗线与耶稣会士所带来的西方版画之“外来影响”的刺激,“无论在南京或北京,这些画家有机会可以见到耶稣传教士所携入的欧洲铜版画,很可能因此刺激了他们恢复具象再现技法的兴趣……”〔13〕高居翰的这一假设是立足于西方绘画与北宋山水画在再现自然之上的某种相似性。即北宋理学影响下的山水写生与西法观察自然的科学之“理”的关联。由此,高居翰得出了西法的“外来刺激”激发了本土传统内部北宋巨障山水的复兴这一结论。
高居翰的这一假设很快受到了方闻(Wen C. Fong)等人的反击,大都以一种“东方学(Orientalism)的幽灵复现”,方闻坚持一种“跨文化的融合观”,进而指出高居翰的“泛西方主义”倾向,直接导致了中西方二元对立的局面。高居翰的最大问题在于建立在“中国画理应发生的虚假期望”基础之上,而忽视了本土传统对于晚明绘画风格革新的重要影响,用了反西方主义的价值观点和诠释法,将西方的风格分析方法强制地套用在中国晚期绘画之上,对其予以批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高居翰的一个认识误区:高居翰的这一假设并非完全否定了传统内部的影响因素,恰恰相反,高居翰试图在“外来影响”的观念之下,重新审视晚明山水画作中所出现的一股近乎抽象且纯粹的力量。并试图重新阐释这一“原创力”的山水风格。高居翰的这一假设所直接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绘画之“外来影响”与北宋巨障山水结构在明清山水中的合流。“这些艺术家都是思虑敏捷、心胸开放的人,他们吸取了外来资源中,那些原来在中国前所未见的绘画观念,为的是裨益自己的创作。”〔14〕需要指出的是,“外来影响”并非个案,正如18世纪时,日本的绘画因借鉴了中国明清绘画的新的质素,从而激活了本土传统中的鲜活生命力,生成了南画。19世纪,西方印象派对于日本浮世绘的吸取,从而在构图与色彩上的创新。20世纪,美国的艺术家受到中国书法线条表现形式的影响,形成了强烈的表现主义倾向。
[清] 弘仁 秋景山水 纸本水墨 122.2×62.9厘米 1660 美国檀香山艺术博物馆藏
二
关于晚期中国绘画尤其是晚明绘画的衰落抑或革新问题,一直颇具争议。大致来说,美国艺术史学界东、西部学派之间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歧,代表着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两派类别。而这些分歧是美国艺术史学的中国艺术研究学界对于如何走向纵深所日益面临的重大问题。
与高居翰的晚明绘画革新论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衰落论的观点,即明清绘画风格的一种普遍论。即晚明绘画已然失却了创新的可能,而是过分因袭传统,陷入了僵化状态,仅仅停留于回溯北宋山水传统的旧形式。美国东部学派的领军人物方闻的老师乔治·罗利(Georg Rowley)就提出一种中国艺术的“普遍性”的观点,进而指出中国艺术的一般性特征长期决定着风格的变化。所有的“创造性”,都统一在这些神秘的一般性特征之下,晚期中国绘画及画家的创作完全是“被决定的、一成不变和毫无自由的”。罗利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文本、铭文及类型学来分析中国艺术的。罗利的研究理路在于借用了汤朴(William Temple)的“自然、人、上帝”〔15〕这一观念,立足于以普遍性探究“中国整体文化趋向”来阐释“何谓中国画”。罗利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古人视自然宇宙为一大生命全体的独特宇宙观和古人感知山水的方式。罗利之于方闻最大的启示在于提供了观看中国画的另一种途径。之后,方闻在老师罗利的“普遍性”观念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推进,力求于山水画的样式和绘画语言中寻求一种本民族艺术的“普遍性”,诸如结构。方闻坚持超越式的东西方“普遍性”融通的可能。方闻的“普遍性”弱化了高居翰的“外来影响”,但却也陷入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怪圈之中。方闻的“误读”在于:高居翰的“外来影响”并非是否定传统对晚明绘画的影响,恰恰相反,他将西方“外来影响”视为一种刺激,重新激活了传统内部复兴的可能。从而出现了晚明绘画作品中所出现的“新颖”创作手法。
东西部两派的不同主张,大致来说,各自代表着海外艺术史研究方法上的两大分野:
一是时代风格的“大叙述”框架,偏重从“外因”考察艺术作品风格革新的时代、地域、背景,以及社会、心理、经济、政治等原初历史语境的分析,讨论特定时代的风格及其分期。如致力于开拓各种研究方法,旨在将海外艺术史的中国艺术研究的外延扩大,建构一种多维视野下的艺术史研究框架。具体到研究方法,从理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研究,继而展开丰富复杂的论述,地域、经济地位、对传统所持的态度,等等。高居翰的主张及其《气势撼人》显然属于此类。一是作品细读的“小叙述”,往往以一幅画的细读,抑或是两幅画的比较研究为切入点,向作品本身的艺术形式的分析挺进,立足点在于艺术作品本身的自足性,阐释艺术作品本身的派别、师承、样式,进而探讨整体艺术史研究序列的演进。方闻及其《夏山图:永恒的山水》则是这一类研究的代表。
后者将研究方法定位于探究艺术作品的形式和风格的历时演进。如方闻的中国山水画(8世纪至14世纪)视觉结构研究,强调“个体”及其“差异性”。他通过择取中国绘画史上带有“纪念碑”性质的经典代表作品,如郭熙的《早春图》、范宽的《溪山行旅》、李唐的《万壑松风》、燕文贵的《溪山楼观》和许道宁的《渔父图》,等等;通过具体的作品阐释其“形式序列”(即风格演化派生的作品),形成了阐释的山水系列样式,如李成样式、郭熙样式及燕文贵样式。具体以《夏山图》为例探讨北宋山水的历史沿袭,通过“物性”联系点、线、面,以此建构中国山水画史的视觉转换机制:结构分析。方闻深受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观念”(idea),李格尔(Alois Riegl)、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的艺术意志(kunst wollen)的影响,即将视觉艺术“意义”的研究推向视觉形象科学的影响。因此,方闻不认同那种将传统西方艺术史研究与表述方法轻易套用在中国艺术研究中的方法(如方闻对于高居翰的“外来影响”研究的反拨)。而是立足于作品本身,专注“小心求证”,中国正统山水画派的发展是一个历代个体演变所参照的创作典范的演变历程,这成为他构建山水画视觉结构的一个逻辑起点。
前者则立足于从艺术作品的外部去考察新的绘画风格革新的原创质素与活力。这使得高居翰往往寻找一系列类型化的画家文化群体的共性。如明清绘画充满了活力与复杂悖论。这些绘画的艺术形式背后承载了怎样的时代信息?明清绘画所蕴含的西方“外来影响”刺激与本土传统的文化张力?遗民画家群体在鼎革易代之际如何面对政治失序的状态?面对新的视觉表现方法,如何调整自身所处的文化语境?高居翰旨在提倡一种跨学科视域下的多维探索,指出某一时期绘画的新颖手法的成因。跟前人相比,明清此一时期绘画风格和题材选择,与传统画史的关联,与当下时代语境所形成的互动关系,以及画家的绘画风格与其所处文化语境,诸如经济条件、社会阶层、交游、赞助人等之间存在互相关联。但是问题在于离开了具体的作品本身,难免又有失笼统之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前者着眼于多维视野的跨学科;后者立足于具体的作品细读;在研究方法上,前者从整体的风格推断演绎,难免陷入笼统;而后者直接从艺术作品本身切入,用作品的比较、归纳,相对具体客观。需要指出的是,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不必陷入孰轻孰重的批判怪圈,其分歧更多是来源于艺术史建构方法及路径的差异。
[宋] 郭熙 早春图 绢本设色 158.3×108.1厘米 107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
因东西学派之间的分歧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归根结底是“艺术终结论”的问题。即:中国绘画在北宋理想型巨障山水达到巅峰,到了宋末大约13世纪就进入了“艺术的终结”,之后的元代绘画开始衰落,至明清绘画所呈现的只是传统的回溯而已,一直处于前人的案臼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艺术终结论”的出现并非是艺术史研究的独有现象,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就指出中国思想史至多不过是垂死的传统主题,因而减弱了中国文化经验的独特性。〔16〕这种“艺术终结论”的观点首先受到了马克斯·罗樾(Max Loehr)与高居翰的批评,高居翰指出:过分强调中国艺术一般性特征,那么势必会忽视革新的可能。晚明绘画并非因袭传统的衰落的百年,而是充满了革新的原创活力,由此带来了“持续百年的旺盛创造力”。“艺术终结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17世纪晚明绘画的个人主义特质及创新精神。
罗樾提出“理性和自觉的创新活动”说,高居翰进一步提出“知性化”说〔17〕,晚明绘画的革新表现在晚明画家以一种双重影响去重新勾连传统与自身处境的内在关联。晚明政治和社会崩解之迫,遗民画家已然失却故国家乡,无居可隐,这带给他们一种全新的体验世界与艺术感知方式,转而将他们对外在社会政治天崩地裂的动荡感知化于画面构成之中,其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在于将自己内心失序崩塌的秩序呈现在画面的构图形式结构里,以此重建理想的山川秩序与政治理想。高居翰的“外来影响”并不是将晚明画家笔下所出现的新颖手法归结于西洋绘画的模仿抑或直接照搬,而是借鉴了一种西方观察自然的新的方法,这一外来刺激使得晚明绘画出现了革新的可能。晚明绘画的革新是晚明画家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创造性转化”传统的绘画风格的革新。之后罗杰·弗莱(Roger Fry)、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接连展开对“艺术终结论”的反驳,他们认为元代绘画并未走向衰落,而是“古中求变”,明清绘画在传统复古的表层之下尚有创新的原创力。事实上,“艺术终结论”所持观点,即自元代之后的绘画走向衰落,这一观念确实有失偏颇之处。在大的传统之下,元代及明清绘画有其独特的创新。如元代绘画笔墨的精纯与文人画的诗意达到巅峰,创造了中国文人画萧散荒寒的至高境界,明清绘画的独创个人主义画风,等等。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西方绘画所带来的一种全新的观察自然的方法,所关涉的绘画与写生“再现”自然之关系命题,到底会给明清画家带来什么影响?明清画家又如何调整自身处境?如何复兴北宋巨障山水“再现”风格?
中西艺术“再现”自然问题的理论渊源则追溯到罗樾的对海外艺术史中国艺术研究影响深远的《中国画的阶段与内容》一文,最初发表于197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举办的中国画国际学术研讨会,他提出了著名的“艺术史三分法”,将中国绘画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汉代至南宋(公元前206—1300)的“再现艺术”,前后历经长达一千五百年的时间。此阶段的风格是作为“发现或者把握现实的一种工具”,视作是“中国画史上从描绘单独事物进步到处理整体空间的阶段”。〔18〕北宋巨障山水的理想山峰代表了“再现”风格的高峰。第二,元代(1279—1368)以后发展而来的“超再现性艺术”阶段,其时宋代的客观再现被主观表现所抛弃。第三,明清时代(1368—1911)的“历史性东方(或称艺术史的)艺术”,其时历史上(传统)的风格开始作为主题起作用,而且被解释为它们就是本来的现实。从罗樾开始,“再现”这一观念成为西方风格学形式分析解读中国绘画发展的一种结构。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是西方风格学的形式分析方法所重视的“时代风格”的影响。“再现”这一观念有其自己的历史发展。因此,成功的风格学“形式分析”必须注意“视觉历史”之“分期”影响。这一观念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自己本身文化背景中所未有的新途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绘画。
明清画家作品中所出现的新颖手法,并非如西方风景一样是为了写实而“再现”(representation),而是立足于自身所处的鼎革易代的原初政治语境,发现了西方风景画与北宋巨障山水在表现自然上的某种相似性。其背后所关涉的“幻与真”这一问题,中西方在自然观与表现物象空间、形体等的差异,西法绘画重“拟真”“视幻”技法、焦点透视及明暗对照法。而中国画是一种“流动的视点”,中国画所要传达和表现的,从来都不是自然的“再现”与空间视幻,而是流动于宇宙空间和万物的“神”与“气韵”,超越了西方绘画的“具象式视觉”(objective view),而是注重把握物象之真。正如上面所一直所讨论的,17世纪晚明绘画之所以出现了一些新的风格质素及绘画创作的“新颖”手法。恰恰是晚明画家面临着一个新命题:在造化与传统之间,如何调整“师传统”与“师造化”的关系命题。如何以自然造化来“修正”现有的传统图式的问题。传统的自然主义的写生在北宋已然发展至巅峰,表现了理想主义的北宋巨障山水秩序。发展至晚明,晚明画家所直面的是如何“再现”自然的问题,即北宋巨障山水的复兴这一新命题的挑战。而晚明的绘画革新创造性地表现在北宋巨障山水的复兴这一文化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设想,高居翰进一步推断正是因为西方“外来影响”的刺激,使得晚明画家得以重新审视自身传统,从而实现了北宋巨障山水的复兴。这一“外来影响”论的研究理路,在高居翰的笔下呈现了一种新的学术可能。正如高居翰在《气势撼人》序中所提出的“阴阳二元的观点来切入中国绘画:一端是在绘画中追寻自然化的倾向,另一端则是趋向于将绘画定型。这两股势力互相激荡,而衍生出其他诸流,直到‘万物’形成”。〔19〕
结语
海外艺术史关于中国艺术风格的“外来影响”研究,其背后所代表的是美国艺术史学界东、西部学派研究的分野,这些分歧是美国艺术史学界对于中国艺术研究如何走向纵深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高居翰所提出的西洋绘画是推动17世纪晚明绘画发展变革的关键因素,从艺术史的脉络来看,高居翰的学术理路带来了另一种艺术史研究路径及可能性,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开创了一种艺术史研究的新范式。这对于中国艺术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与研究启示。海外艺术史方法论的创新给国内学界很多的教益,但是也要警惕学界一些忽视研究对象本身而专注于新方法尝试的现象。艺术史路径选择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应立足于本土具体的文化场域和原初语境,在坚守自身边界的基础上,并寻找学科的融通,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无疑是未来所趋。
注释:
〔1〕海外艺术史译介的鼎盛时期代表作有:尹吉男主编的《开放的艺术史》丛书,李军主编的“眼睛与心灵:艺术史新视野译丛”与《跨文化艺术史》,范景中主编的《美术史的形状:美术史研究所丛书》,牛克诚、杭春晓、张南南主编的《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第一辑)》,巫鸿、郭伟其的《世界3: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等等。
〔2〕海外艺术史的“外来影响”这一选题需从外部思潮和内部画面表现两个层面来展开多维透视。本文为海外艺术史路径、方法和问题的讨论,关于外来影响与明清山水的再发现及其新颖手法的表征这一问题,将另文专论。
〔3〕Yonezawa Yoshiho. Painting of Ming Dynasty, Tokyo, 1956, pp.31-32.
〔4〕Michael Sullivan.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3, p.64.
〔5〕[美] 高居翰著,李佩桦、傅立萃、刘铁虎、任庆华、王嘉骥译《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页。
〔6〕[美] 班宗华著,白谦慎编,刘晞仪等译《班宗华画史论集:行到水穷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32—347页。
〔7〕同上书,第336页。
〔8〕参见1981年高居翰编选的《班宗华、高居翰、罗浩通信集》(包括十四封通信和三篇书评,另收录罗浩《詹景凤论吴门画派》和高居翰的四篇论文),第17—18页。
〔9〕同〔5〕,第100页。
〔10〕石守谦《对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再现论述模式的省思》,载《朵云》第六十七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11〕同〔5〕,第1页。
〔12〕[美] 高居翰著,李佩桦、傅立萃、刘铁虎、任庆华、王嘉骥译《山外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0—141页。
〔13〕同〔5〕,第141页。
〔14〕同〔5〕,第6页。
〔15〕William Temple. Nature, Man and Go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35.
〔16〕John King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1949-1965. 1987, pp.6-7.
〔17〕[美] 高居翰著,李佩桦、傅立萃、刘铁虎、任庆华、王嘉骥译《江岸送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
〔18〕[德] 罗樾《中国绘画史中的基本问题》,载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 no. 2 (February 1964),第1921页。在本书中,罗樾提出把中国绘画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的经典论断:第一是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装饰性艺术”,风格是形式上的;第二阶段是从汉代到南宋的“再现性艺术”,风格是发现把握现实的一种工具;第三个阶段是元代至清代的“超越再现性艺术”,此时,由宋代再现转向元代的主观表现。参见罗樾《中国画:阶段与内容》,收入《中国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年版,第286—297页。
〔19〕同〔5〕,英文原版序,第9—10页。
宋石磊 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1期)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