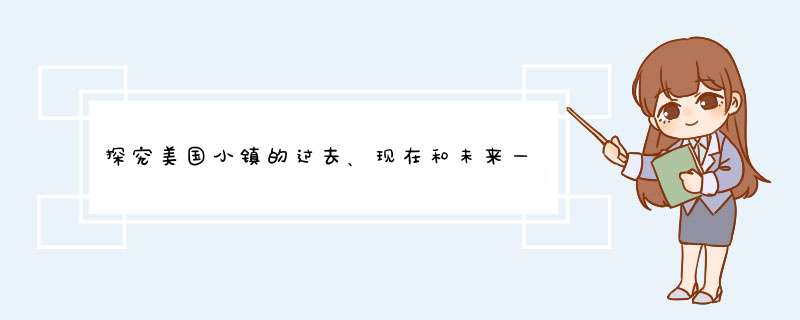
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美国知名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原社会学系主任、荣休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46年出生于堪萨斯州,1968年在堪萨斯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7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亚利桑那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出版专著30余本,代表作包括《重塑心脏地带: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部》(Remaking the Heartland: Middle America Since the 1950s,2013)、《小镇美国:现代生活的另一种启示》(Small-Town America: Finding Community, Shaping the Future,2015)、《留守者:美国乡村的衰落与愤怒》(The Left Behind: Decline and Rage in Small-Town America,2019)等。曾因教学和研究成果获得多项荣誉和奖项。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美国城市,关于乡村的甚少。近年来,由于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城乡矛盾突出,乡村问题引起越来越多关注。要了解当代美国,绕不开美国乡村小镇。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 《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的:“小镇是美国这个民族的力量所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始于小镇。”
罗伯特·伍斯诺教授是一位有较高知名度的美国社会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美国乡村问题,尤其是通过大量实地采访和多年追踪研究,出版了多部聚焦小镇社会变迁的专著,从文化层面上阐释了美国小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近日,记者采访了伍斯诺教授,听他讲述美国小镇的发展现状、当地民众的想法和认知、小镇在当今美国社会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探索、研究和实践。
社会学方法论:深入调查和定性访谈
《中国社会科学报》:首先,请分享一下您是如何开始学术生涯的?在堪萨斯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的社会学训练,对您之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伍斯诺:我在堪萨斯州一个小农场长大,一直认为自己长大后会成为一名农民。然而,大一那年父亲过世了,这迫使我重新思考今后的出路。我觉得自己没有哪方面特别突出,所以就想着今后或许可以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在本科选专业时我经历了各种艰难的尝试,考虑过商学、经济学和心理学,但在读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的著作后,便开始学习统计学并对社会团体感兴趣,最后选了社会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期间,由于当时正赶上校园反叛运动,收获不如预期,所幸还是适应了校园文化,也遇见了几位好教授并得到了他们的指导。
对我帮助较大的一位教授是查尔斯·格洛克(Charles Glock),从他那里我了解了调查研究,并与他一起合编了一本关于青少年偏见的书。我还跟随钱德勒·塞兹尼克(Gertrude Selznick)教授研究种族关系,选了特罗伊·达斯特(Troy Duster)教授一门关于黑人民族主义的课。这些都让我十分受益。在确定研究课题时,有好几个月我经常去隔壁的研究生院神学联盟(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听课,并与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们交流,也阅读了不少神学方面的文献和著作。我从尼尔·斯梅尔瑟(Neil Smelser)和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两位教授那里进一步学习了相关理论。如果没有格洛克和贝拉等几位老师的引导,毕业论文我应该不会选宗教意识这个课题。
韦伯和涂尔干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我的研究深受韦伯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影响。对涂尔干尝试把社会学变成一门科学的做法我并不赞同,但他对道德共同体的研究让我受益匪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简单概述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或理论吗?
伍斯诺:我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不拘一格。我做过很多全国性的调查,并十分看重定量分析,但对民调持批评态度,因为它们的有效返回率太低,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实现精确统计分析。我主张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尤其重视定性访谈、民族志研究和历史信息,与其匹配度最高的是实践理论,它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著作中演变而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及美国其他实用主义者和道德哲学家们的著作,如今已成为美国社会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实践理论强调社会互动、情境、控制力和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都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田野调查在实际 *** 作层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访谈人的身份是否会影响受访人的态度与回答的内容?如何平衡这些影响?
伍斯诺:我认为进行田野调查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把研究置于情境中,即事先做好功课,对当地的文化规范、历史和经济水平等要有基本了解;(2)对自己研究的目标和具体问题等细节要十分明确;(3)采用配额设计,以确保采访对象能合理覆盖不同种族、社会阶层、性别和年龄的人群;(4)遵循以人为研究课题的所有程序,包括得到被研究者的同意;(5)诚实地说明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并允许受访者就此研究提出问题或决定是否参与;(6)从非正式的交谈和进行试点访谈开始;(7)在访谈过程中认真做好现场记录,及时记录下第一印象;(8)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你采访过的对象进行匿名处理,这样对方更愿意畅所欲言;(9)不要急于关注主题和概括性的东西而忽略了受访者使用的具体词汇;(10)对与其他研究人员或助理合作保持开放态度,他们有助于平衡你的观点。
许多刚入门的研究人员在进行定性采访时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在概括了五六个要进行的主题后就不再做更多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这往往会影响后续进展,使采访结果不尽如人意。对我来说,通常一个约60分钟的采访需要准备10—15页的详细问题和后续问题,在实际访谈过程中不一定每个提问都用到,但准备充分可以促使采访人对访谈内容预先进行认真、仔细、全面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研究主要关注宗教、公民社会和社群、文化社会学这三个领域。请问这三者有何关联?
伍斯诺:这些都可称为“软”话题,即如何定义它们、测量它们以及如何解释结果都存在争议,也很难对它们作精确研究。然而,这类话题引起了包括韦伯、涂尔干和托克维尔在内的一些开创性学者的兴趣,至今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学研究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些话题相互交错,因为宗教是文化的,由社群组成,同时也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社群可以说也是如此,它们是文化建设的场所,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话题,正如涂尔干所说,也意味着道德义务。它们引导、促成和约束我们作为个人、家庭成员和朋友的行为。所以,这些领域的研究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调查可以对所有成员进行归纳并研究变量间关系;定性访谈可以探究个人的独特经历及其话语;背景和历史信息使我们得以洞察社会变化的遗产和轨迹。
我在研究中从未尝试创造一种可称之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我志不在此,认为这样做更多是为了“沽名”,且容易作茧自缚、缺乏多维视角。然而,一些主题会在我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社区就是一个重要主题,因为我相信个人主义常常是一个社会问题,而社区强化了公民社会并深刻塑造了我们作为个人作出的选择。社区也让我着迷,从亲密的家庭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周边,再到我们所生活的更大范围的跨国大环境,在这些不同层面我们都能够体验到社区的魅力。
美国文化的基石——小镇的韧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过去10年间,就小镇/乡村这个话题您出版了5本书(《重塑心脏地带》《小镇美国》《粗野之地:得克萨斯州如何成为圣经地带中的最强的州》(Rough Country: How Texas Became America’s Most Powerful Bible-Belt State,2016)、《留守者》《血统:理解美国乡村家庭》(In the Blood: Understanding America’s Farm Families,2020))。请简要概括一下这些年来您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伍斯诺:《重塑心脏地带》重点关注位于密西西比河与落基山山脉之间的11个州,考察了那里的农业、肉类加工业、中西部文化形象的变化,以及从小镇到诸如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这样的大都市等不同地区人口的变化。这本专著通过历史案例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内战以来堪萨斯州的宗教和政治作了深入探析。我又考察了内战期间已加入南部邦联的得克萨斯州的宗教和政治,以作比较研究,《粗野之地》是这一研究的成果。《小镇美国》分析了人口发展趋势和小镇居民对自己生活变化的看法,该研究基于数百次定性采访和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血统》也是基于大量的定性采访(采访对象为四个地区约200户农户)。《留守者》是一本为非专业读者撰写的通俗读本,书中提供了一些说明性案例研究,是对之前研究的总结。
简言之,这几本书的主要结论包括:(1)乡村县和人口低于2.5万的共1.4万个小镇占美国人口的17%;(2)这个数字(分别为5000万人和6000万人的总人口数)相对稳定,虽然相对于城市和郊区而言美国乡村的人口数量有所减少,但其绝对人口数量并没有下降;(3)乡村人口随美国人口普查定义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在得出相关结论时一定要谨慎;(4)乡村人口更多集中在中西部、南部和山区,在美国沿海相对较少;(5)与城市人口相比,乡村人口中白人占比更高,黑人占比更低,西班牙裔人口总体有较大幅度增长;(6)在文化和经济上,乡村人口呈现多样化特征,从专注于高科技产业和农业经济的小镇到以采矿为主的贫困小镇,从白人占绝大多数的社区到西班牙裔占大多数的社区,等等;(7)小镇的特点与当地社区密切相关,居民对所在社区的价值观有着强烈的道德义务感;(8)小镇居民对其生活方式日渐衰败感到担忧,并且经常感到受都市趋势,以及联邦政府决策时似乎更偏向城市的政治问题的威胁;(9)由于美国的联邦政府体制,乡村地区对州和国家政治有着人口不成比例的影响;(10)人口下降的乡村地区往往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它们与老龄化、医疗保健不足以及无法获得其他社会服务等问题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美国小镇有何特点?您的关注点主要在哪方面?
伍斯诺:尽管小镇和乡村地区的人口和经济特征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我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是把这些特征作为背景进行考察,即生活在小镇的人们如何适应、感知和选择的背景。例如,我一直很感兴趣地倾听人们谈论当镇上的学校关闭时,当他们不得不开车到更远的城镇去看医生时,当孩子为找工作而搬离小镇时他们的感受。与此同时,对新移民如何在小镇安家,人们对慢节奏生活方式和邻里间相互认识这种文化的重视,为什么他们经常能够发现看似贫瘠的地方的美,我也一直有兴趣了解。许多故事听了令人心酸,背后诉说着当地居民的艰辛,也体现了他们的韧性。
小镇居民与其他地区的美国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在同样的快餐店吃饭,在同样的折扣店购物,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在同样的选举中投票。但是,小镇居民对自己的社区非常忠诚。如同城市居民可能对来自芝加哥或纽约而感到自豪一样,小镇居民也为生活在鲜为人知的地方而感到自豪。他们认识所属教堂里的每一个人,支持当地图书馆,谈论最近一场足球比赛,在杂货店遇到街坊邻居时都能叫出对方的名字,等等,这些都让他们感到自豪。小镇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一种昔日美国曾有过的联结,是一个人们熟悉所有一切的地方,但也要求居民们具有责任感,那种出自己的一份力来帮助邻居和做一名负责任的公民的责任感。
小镇一直是个可以更深入认识社群的场所。在小镇,一个人对自己从事什么工作、有何爱好以及政治上做怎样的决定往往无法避开他人的影响。换言之,由于是一个熟人小圈子,他们深受社区其他人的影响,而且也重视这种“归属感”。当他们认为自己社区所代表的价值观受到威胁时会感到忧虑,并相信这种威胁是对整个社区的威胁。因此,他们常常批评联邦政府,因为政府离他们太远,总是偏心于城市、照顾城市地区居民的特殊利益,以及干涉他们看重的当地的自由。出于这些原因,小镇居民有时倾向于在总统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他们认为会改变体制的“局外人”或“特立独行者”。因此,那些来自城市(占大多数)的总统候选人经常以“局外人”自居,或者强调自己来自住在小镇的家庭。例如,里根和卡特总统都自称是政治局外人并强调自己的小镇出身。
多样性和复杂性
政治极化和城乡分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开始研究小镇并在撰写《小镇美国》时曾提到,您“最大的愿望首先是期望大家对小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更好的理解,其次是期望大家对小镇能多一份尊重,对小镇为这个社会的贡献多一份感激”。自您开始研究小镇以来,您觉得它们发生了哪些变化?您现在的愿望有改变吗?
伍斯诺:我刚开始进入这一领域时,几乎还没有其他社会学家就“小镇”或乡村社会学做过长期研究,相反,几乎每个大学的社会学系都认为应该开设城市社会学课程。更糟的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表明城市化是唯一重要的趋势、认为很快大家都会居住在城市的相关图表,好像乡村人口根本不存在似的,即使存在,也纯粹是无趣的、不值一提。然后就有了2016年的总统选举,面对突如其来的结果,专家们(错误地)认为大选结果是由乡村选民决定的。因此,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到美国乡村去一探究竟,看看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想找出症结所在。他们通常在纽约找人,派到艾奥瓦州或密西西比州,再和那里的人聊上几个小时,然后下结论。这样的结论往往带有贬义,言下之意不外是乡村地区的美国人是愚蠢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已经与进步开明的人脱节。那时我已完成了这方面的研究,所以《留守者》是本小书,简要总结了之前相关研究的观点。现在的专家学者们对小镇确实有了更多的了解,不是因为我的书,而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小镇的学者开始多了起来。
研究这一领域的一个长期困难,是美国人口普查对乡村、城市的粗略区分和媒体过度强调差异性,这加大了城乡鸿沟。例如,大部分关于美国乡村的文章都基于被定义的“乡村”县,而没有更多地关注这些县之间的差异,或者基于乡村居民对小镇的认同感远超他们对所在县的认同感这一事实。问题是,正如我们社会学家所说,“类内差异”(within-category variation)与“类间差异”(between-category variation)一样多或更多。换言之,“美国乡村”不是“一码事”,正如“美国城市”不是“一码事”那样。实际上,就历史和地形而言,美国乡村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可能有着天壤之别,包括人们工作的经济类型(林业、采矿业、畜牧业、粮食种植业、轻工业)、族裔、社区规模、职业和收入。例如,我在《血统》一书中曾写到,一些农民过着勉强维持生计的日子,竭力在家庭范围内留住小农场,而一些农民则在使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卫星定位的拖拉机,用以耕种数千英亩的农田。有在几英亩土地上精耕细作有机蔬菜的,也有动则出口数千吨小麦和玉米的。同样,在人口过千的小镇上,有人为帮助年迈的父母而选择留在小镇,不得不住着过时的房屋,而在人口达到2.5万的小镇上,有人在需要研究生学位的专业岗位就职并领着高薪。所有这些差异反映了美国乡村的复杂性,而并非传统刻板印象那样千篇一律。
庆幸的是,目前出现了新一波面向该研究领域的高质量奖学金。关于小镇如何受到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肉类加工业、学校合并、政治、技术和移民的影响,已经有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与此同时,小镇内的变化没有那么大。规模更小的镇继续面临着人口减少的问题,而较大的镇人口总体保持稳定,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呈增长态势。然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社交媒体和卫星技术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机会,他们生活在小镇的同时还能从事更多样化的职业。此外,通过与其他城镇的联系,小镇的高质量中等教育(高中)从对方提供的课程中获益,小镇医院与大型医疗中心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小镇居民们从未疏远或断开与城市中心的朋友、家庭、新闻、娱乐及媒体的关系,而如今这些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么看美国政治极化的现象?这与城乡分裂有何联系?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乡村地区政治生态有何变化?
伍斯诺:美国政治极化很严重,这个问题在近半个世纪始终是个大问题。1980年以前,南方乡村大部分选民投票给民主党,而中西部乡村选民大部分投给共和党,但1980年以来,这两个地方的乡村选民多数都投给了共和党,这意味着城乡分歧与两个政党之间的分歧相吻合。宗教领域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在《红州宗教:美国心脏地带的信仰与政治》(Red State Religion: Faith and Politics in America’s Heartland, 2014)一书中,我分析了堪萨斯州如何变得更加坚定地支持共和党,因为保守的天主教徒和保守的新教徒联手反对堕胎,而在该州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很多事情上都没达成过一致。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负差距通常很小,小到任何一个小群体的团体性决定都足以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反对堕胎和同性恋的“福音派”(保守派基督徒)经常被认为是助力共和党人获胜的功臣,而福音派人士往往生活在小镇和乡村地区。换言之,城乡鸿沟有时与福音派—非福音派的分歧十分吻合。共和党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引发了人们对乡村人口是否是决定性因素的猜测。与2016年大选相比,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城乡差距受到的关注要少很多,原因可能是民主党候选人获胜了。
作为社会学家对大数据和疫情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学生时代到现在,就理论和研究方法而言,社会学领域中发生了哪些较大的变化?如今,大数据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学术领域,请问这对社会学有哪些影响?
伍斯诺:不幸的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变得过度自恋:鼓励学者为小众写作、玩概念游戏,创造一系列让现实世界变得更晦涩难懂的概念来追逐功名。好在最优秀的社会学家抵制了这种趋势,转而专注于收集和分析有关重大社会问题的信息,如不平等、种族、性别、家庭、社区、移民、国际关系和刑事司法。庆幸的是,大数据让学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定量数据,而且为人种学和历史学提供的研究基金也越来越多。尽管民意调查的数据大多毫无价值且不可信,但不少机构收集了许多高质量的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而且也有了更好的统计分析方法。大数据通常是对这些方法的有益补充。如今,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搜索和电子邮件方面的数据有很大研究价值。当然,谁可以获得这些数据的访问权限也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006年关于专著《美国神话:为什么我们竭尽全力建设一个更美好国家的目标没有实现》(American Mythos: Why Our Best Efforts To Be a Better Nation Fall Short)接受采访时,您曾提到,“对我而言,最持久的影响可能是提高了我作为社会学家的意识,即我们如何从文化上理解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灾难”。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您如何看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伍斯诺:包括我在内,没有人预料到会出现像新冠病毒这样具有破坏力的东西,并以现在这样的方式占领世界。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极度恐惧:对恐怖主义、疫情、环境破坏、核毁灭等灾难的文化反应》(Be Very Afraid: the Cultural Response to Terror, Pandemics, Environmental Devastation, Nuclear Annihilation, and Other Threats,2010),探究了以前的大流行病和自然灾害,并指出,当灾难发生时会有一种强烈的要“做些什么”——“做什么都可以”的心理冲动,以“行使代理权”并重新获得某种掌控感。正如书中所言,这种倾向会导致反应过度、反应不足或错误的行为等各种后果,有时后果是毁灭性的。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基于准确信息的深思熟虑的理性行为。我们也看到了在当前大流行病暴发的情况下,由于公共卫生官员对这场危机的评估,以及科学家们通过创新研究作出的回应,采取的一些基于信息的深思熟虑行为的价值。碰巧的是,保持社交距离和遵守隔离限制在心理上也是有益的。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应对为阴谋论者推动错误信息的散播提供了绝佳机会,从而受到政治极化的负面影响,结果让处理本应该更容易解决的问题变得困难重重。
不过,它也带来了更广层面的有意思的结果,包括技术让人们不必面对面而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在线见面。很多人认识到,我们无须花费巨额资金和浪费时间旅行,网上也可以进行良好的对话和有效开展业务。当然,这次大流行病也再次强有力地表明世界许多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年来,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出版有中长期规划吗?您对青年学者有何建议?
伍斯诺:在学术生涯早期,我在完成毕业论文并陆续出版了几本书后,从调查研究转向历史研究并立志开启“十年项目”。随后十年间,我撰写了一些关于西欧重大文化变迁的论著,进而获得了一些研究基金。我第二个十年的研究得益于此,研究主题大部分集中在宗教领域,这也使我有机会研究美国宗教和艺术、移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同时激发了我对话语分析和实践理论方面的兴趣。此后,我根据自己在堪萨斯州的成长经历及与此相关问题的聚焦,做了中西部社会变革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研究基于小镇、乡村和乡村生活这些话题的大量采访。最近,我又回到宗教社会学。
对青年学者而言,一开始研究课题的选择非常关键,研究任何东西至少需要5—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它应该是研究者真正关心并怀有极大热情的课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褚国飞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