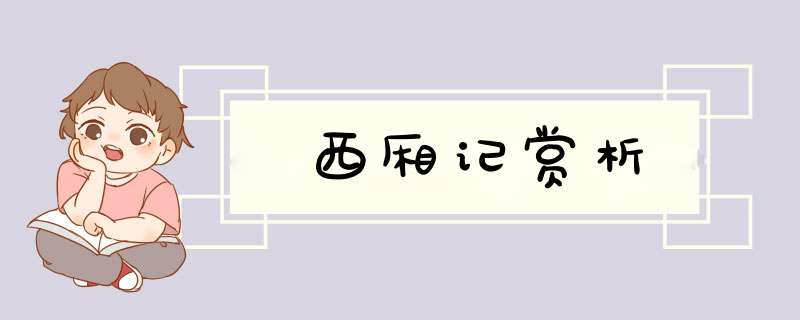
赏析:《西厢记》原名《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是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的杰作,也是元杂剧中最优美宏伟的大型喜剧。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
《西厢记》可以说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它以五本的宏大规模来敷演一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不仅题材引人喜爱,而且人物能刻画得更丰满细致,情节能够表现得更曲折动人,再配以与浪漫的内容相称的秀丽优雅而又活泼的语言,自然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
《西厢记》主要讲的是书生张珙游学河中府,在古刹普救寺与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小姐相遇。因一见倾心,借宿在崔氏眷属暂住的西厢院外僧房之中。夜间莺莺花园烧香,强生隔墙吟诗,莺莺亦酬诗一首;张生继而藉崔府超度老相国时,追荐自己的父母,在法会上与与莺莺再度相见。其间贼将孙飞虎为抢夺崔莺莺,兵围寺院,崔母求助于寺众,许诺能退贼兵者以莺莺相配;张生应下此诺并修书一封请惠明送至友人白马将军杜确处。杜确率兵打败孙飞虎,普救寺兵围虽解但崔母却违约赖婚,命两人兄妹相称,张生因此相思入病,侍女红娘遂教张生夜间在花园外d琴,封莺莺诉说心曲。红娘为莺莺、张生传书递简,莺莺瞒过红娘而“待月西厢下”,是夜张生依约到来,但莺莺毕竟囿于礼教,又被红娘看见,竟翻脸不认。张生为此抑郁成疾,莺莺不禁内疚,以药方为名托红娘送去,当晚便由红娘送莺莺到张生房中。月馀后,两人情事被崔母发觉,崔母大怒拷问缸娘,红据理以争,认为崔老夫人不应悔婚,若不允婚只怕还有玷辱家门和治家不严的罪名,崔母只得允婚,但张生必须应举得官方能迎娶莺莺,两人因此长亭送别。强生行至草桥,见莺莺追赶而来,醒后才知是梦境。张生得中后欲与莺莺完婚,被当年曾经与莺莺订亲的崔母内侄郑恒阻挠,恰好白马将军携旨到达,为张生与莺莺主婚,郑恒羞愧自尽,有情人终成眷属。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剧本写红娘催促她回避,而她的反映是: 回顾——觑末——下。请注意这一舞台提示,它异常强烈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把箴规抛之于脑后。通过一细微的却是引人注目的举动,作者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
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 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
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
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当观众看到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都会哑然失笑。在作品中,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奏,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诚挚的追求。他是一个“志诚种”。志诚,是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内核。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