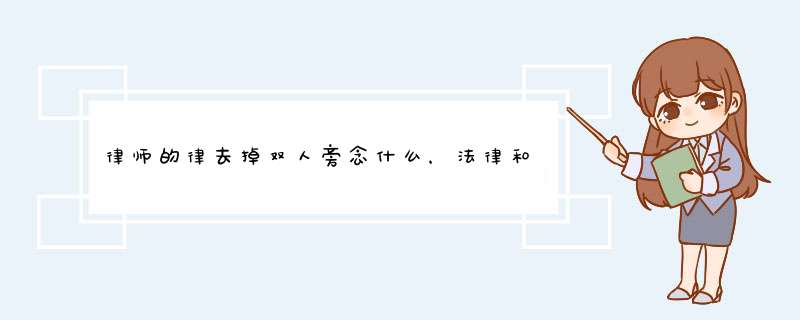
“律”字甲骨文结构与现代汉语相同,左“彳”右“聿”。
“ 彳”就是行的半边,指代行。行的甲骨文为

,是一个十字路口,意思是顺道而走、而行。因此行有执行、践行之意。《广雅·释言》说:“律,率也。” 《中庸》说“率性之谓道”,朱熹注:“率,循也”。
宋均注《春秋元命苞》:“率,犹遵也”。 因此律有遵循之意,而这一意就是由“彳”所发出。
但是,遵循、践行只是一个动词、动作,其本身是空洞的,关键在所遵循和践行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就是右边的“聿”。也就是说,整个“律”字实质上是一个动宾结构,左彳是动词,右聿是宾语。因此,释读“律”字的关键,在于对“聿”的释读。
“聿”的甲骨文字形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形态于“尹”字同。对于甲骨文“尹”字我们在前篇文章中进行了释读,其字形是由右手握笔之象,呈现书契刻画者正在刻画书契的场景。刻画书契就是签订契约,而书契刻画者是契约双方的中保,不仅具备书契刻画技术,更重要的还要德高望重。
因此,“尹”的原始意义有两个,一个是用作动词,一个用作名词。用作动词是帮助别人订立书契、契约,用作名词是帮助别人订立书契、契约的人。即便是现在,契约、合同也是维持人与人良好关系,实现社会良好秩序的基本工具。因此,作为中保帮助别人去订立契约实际上就有治理社会的含义。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周易·系辞》为什么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里的“百官”是“百工”,即各行各业。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句话明确说明,结绳的本质依然是契约、合同,书契只是契约的升级版。这意味着契约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中,具备基础与核心地位。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中国文明的契约特征是异常突出的。契约不仅首先在中国文明出现,而且远远早于其他任何文明,包括所谓的古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
而现代人却想当然地认为,以契约为中心社会秩序只是现代文明才有的,契约秩序的实现需要以现代政府的出现和现代法律制度的出现为前提。而中国的历史事实是,在政府和法律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中存在一个漫长的书契时代,长达数千年,甚至上万年。
在书契时代,没有政府,没有法律,但是却有书契、契约,而且仅仅凭借书契,人与人之间就可维持良好协作关系,整个社会就可维持良好秩序。这就是“书契之治”。
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不要看到“书”字就和语言化的文字,就和纸笔联系起来。“书契”之“书”和语言化的文字没有任何关系,和纸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语言化的文字,以及纸笔的出现,远远晚于“书契”。“书契”之“书”,用作动词是指用刀在木头上刻画书契文,用作名字就是指书契文。
语言化的文字就是与语言密切联系的文字,就是语言的符号化,也是现代一般意义上文字。现代社会最大的一个谬见就是把语言化的文字当成文字本身,把语言化文字的起源当成文字本身的起源。说什么古两河的楔形文字是人类最早文字,其次是中国的甲骨文。其实,无论西亚的楔形文字,还是中国的甲骨文,都非文字的初始状态,而是文字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也是整个人类的文字的初始状态是书契文。人类文字起源于中国的书契时代。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甲骨文“文”字就是两排契齿纹的交错,文就是指书契文,就是指书契。“文明”就是因“文”而“明”,也就是因“书契”而“明”。故而,“文明”就是“书契明”。同样,“文化”就是用“文”去“化”,去教化。也就是用“书契”去“化”,去教化。
对远古时期漫长的书契时代,在中国最主流的传世文献中,在《五经》中,尽管信息很少,但却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传统的中国人也深信不疑。“三皇五帝”的历史框架就是建立在书契时代的基础之上,“三皇五帝”时代就是书契时代。只是到了“五帝”时代,书契秩序开始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其伟大之处都是在于,拼命抵制外来文化,努力捍卫中国自身所固有的书契文化。“三皇”时代的书契秩序更纯正,“五帝”时代书契秩序开始变得残缺。因此,“皇”比“帝”更伟大,更美好。
中国文明起源于书契时代,书契是中国文明的基石和母体。对人类而言也是如此,即人类文明也起源于书契时代,书契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和母体。中国因书契而进入文明,中国之外的地方因为文明的交流,直接和间接接受中国的教化而书契化,也随之逐渐文明化。
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中文本义上的“文明”、“文化”,中国之外的所有地方,在所有时期,都不曾出现。因为,书契时代仅仅在中国历史中出现,“文”也仅仅起源于中国历史,为中国历史所固有。现代意义上的中文“文明”、“文化”,严重被西化了,英语化了,与传统意义有本质不同,更多地是指一种生活方式,以及按这种生活方式生活的地区和人民。
然而,令人痛惜和惊诧的是,对于中国和人类文明拥有如此基础地位的书契时代,现代人却选择了无视和否定。不真正理解书契时代,不仅仅无法去真正认识和理解人类文字的历史和本质,更重要的是,也无法真正理解人类文明自身,无法理解人本身。
中国之外的西方人,他们对书契时代选择无视和否定还是有谅可原的,因为在中国之外的西方本来就不存在书契时代。没有书契时代,就意味着西方缺乏文明核心要素起源的历史,缺乏“文”的起源的历史。因此,有史以来,中国之外的西方人都是认为文明的核心要素都是由神所创造的,是神所赐予的。无论古两河古埃及,还是后来的基督教,都是如此。唯有中国一直认为文明的核心要素是由古人基于经验所创造,并一代一代传承。
对于现代的中国人,跟在现代西方人屁股后边,也开始对书契时代选择无视和否定,对“三皇五帝”的历史进行无视和否定,就是不可饶恕的,就是辱没祖先,是数典忘祖。然而更讽刺的是,本来“数典忘祖”是大逆不道的,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但是在现代的中国,也似乎快成褒义词了。
书契实质上是一种信用保障工具,简单地说,是一种信用工具。契约时代实质就是信用时代,书契之治实质就是信用之治,书契秩序实质就是信用秩序。
信用秩序之所以会出现,其根本并不在于作为信用保障工具的书契的发明和应用,而是在于当时的中国人本身就是高诚信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是高度重视个人诚信,把个人诚信看成个人立身之本,看成社会存在之基石。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远古时代,就开始将个人诚信做为个人和社会之核心,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在那时就对世界的稳定性建立良好的信心,从而对人本身建立良好的信心。《易传》说“乐天知命”,《左传》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说“天视听自我民视听,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这里的“天”就是“自然”就是“世界”。天是绝对的善,值得人去绝对信赖。
也正因为天是绝对的善,值得绝对信赖,它也就变得绝对不重要,无需人去关心和理睬,更无需人去干预,即所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人唯一需要关心和重视的是人自身,去做好人自身,去诚信。人的问题,核心就在诚信。
一部易经其实就是围绕一个“贞”字而展开,即“元亨利贞”之“贞”。“贞”就是“守正”,“正”就是人的本心本性,“守正”就是《中庸》“率性之谓道”之“率性”。《中庸》还说,“诚者天之道”,因此,“诚”、“率性”、“贞”,是同一回事,都是“道”。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易·系辞》总结说:“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吉凶并非绝对外在的,不存在绝对外在的吉凶,人自身的内在的“贞”才是外在吉凶的决定者,只要你“贞”了,最终结果一定是吉的。天地的存在也是在贞,即遵循和坚守天地自身的本性,做真实的自己。因此,天地的存在也是在展示贞的道理,即“贞观”。日月也是遵循和发挥自己的本性,做真实的自己而发出光明,因为发光是日月的本性。总之天地万物看似缤纷复杂,但是它们的存在都是在顺应和坚守自己的本性上,在贞上,却是统一的。
在这一点上与古两河古埃及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照。他们对世界的稳定性缺乏基本的信心,认为世界是高度不稳定的,人类时刻面临被灭绝的危险。也正是对世界的稳定性高度不信任,导致他们对人自身玩法建立信心,同时也产生幻觉,认为世界是受世界之外的某种力量所创造和 *** 控,构造出了神和宗教。
宗教起源于对人自身的高度不信任,同时,对人不信任也一切宗教的核心特征。对人的不信任相应的是,对虚幻的神的信任。信神不信人必然导致,人们重视神,而轻视人;重视神的生活,而轻视人的生活;重视神的天国,而轻视人世。
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是一种低信用、低信心文化,这种文化显然无法出现以个人诚信为基础的个人关系和社会秩序,不可能发明契约,建立契约秩序。
直接起源于西欧的所谓的现代文明,号称是反宗教的,具体是反基督教的,但是,也并未出现对人自身的真正信心。现代文明对人自身依然是高度不信任的,在这一点上,完全继承和延续了宗教时代的做法。现代文明的基石是科学和民主,而非人的诚信。科学是科学真理,民主是民主制度,都是现代人所虚构的,赖以增强人的信心的东西。
现代人骄傲地认为,宗教时代的神是虚幻虚构的,信仰虚幻虚构的神是愚昧和迷信。认为现代的科学真理和民主制度与宗教时代的神本质不同,都是客观真实的,而且可以保障和增强人的幸福。其实,科学真理和民主制度、人权制度,和宗教时代的神并无本质区别,也是被人所虚构出来的。信仰科学和民主,与信仰上帝并无本质不同,都是以对人自身的不信任为基础,都是愚昧和迷信。
因此,从本质上说,现代文明的出现并非是对宗教的彻底否定和摆脱,而只是一种宗教改革,对过去的宗教有良好的继承。现代文明其实是一种新的宗教形态,科学和民主,以及由其所派生出来的资本主义,都是新的神,现代科学其实就是新神学。
唯有对人自身高度信任,以个人诚信为基础的文化,才是真正非宗教的。一旦对人自身建立真生的信心了,以个人诚信为考虑重点和中心了,人也就自然不会去虚构一些外在的东西,去增强人的信心了。唯有此时,人才能真正摆脱愚蠢和迷信。即唯有对人自身的信心、信仰,对个人诚信的信心和信仰,才是明智的,才是不迷信的。
前面是铺垫,下面开始进入正题,释读甲骨文“聿”。
“聿”的甲骨文有两种字形,一种字形和“尹”等同,是不太常见、非常态的字形。第二种字形的字形的主体依然是“尹”,但是却在代表刻刀的竖线上加了“八”字符。而甲骨文“律”字的“聿”也是带八字符的。这意味着,带“八”的聿,才是其常态字形。
因此,总体而言,“聿”字就是加“八”的“尹”。前面我们已经释读了“尹”,现代的关键就是弄明白“八”字符的意义何在?

《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八”是“分”字之初文,本意为分。后被借用为数字八,加刀为“分”。《尔雅·释器》:律谓之分。疏曰:律一名分。《说文解字》: 律,均布也。显然,律的分、均布之意,来自“聿”字中“尹”上的的八字符。
这意味着分、均分是“聿”的重要特征,也是“尹”的重要功能,这体现书契的订立和纠纷的处理过程中。
前面说过,“尹”字本意有二。一个是书契的订立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中保的参与,中保不仅在技术上刻画书契,而且还要帮助契约双方达成共识条款,并且作为证人。“尹”字的名词就是指中保。作为中保的“尹”,不仅懂得书契的刻画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德高望重,道义道德水准很高,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为双方评理。
无论在书契的订立过程,还是在订立之后的执行过程,双方之间如果出现分歧,可能都需要作为第三方的“尹”来出面调停,评理,以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共识。“尹”的调停过程,就是在双方之间消除分歧的过程。如何才能消除分歧?关键在于公正、公平,而且双方都是认可的公正公平。即《说文解字》所说的“律,均布也”。
书契是一种信用保障工具,而从根本上来说,信用的基础是契约双方自身,来自双方自身的诚信,并非来自书契。从技术上说,信用就是对书契条款的遵守。但是,书契条款并非外在规定,而是契约双方之间的共识。即便作为中保和调解人的“尹”,在共识达成的过程中可能会起重要作用,但是,其作用和书契一样的,是外在的。共识的真真主体是契约双方自身,中保的作用只是增加理解和互信。
因此,“聿”的原始的核心内涵应该是契约双方所达成的共识条款,对于这个条款,双方有必须遵守的义务。这也是“律”的核心内涵。
“律”是以个人诚信为基础的,基于完全自愿自主原则的,人与人之间所达成的共识,而非独立于当事人的,外在的权威规定。人之所以要遵守“律”,原因在于,这个律是经过我认同、接受和承诺的,其权威性就来自我自身的认同接受和承诺,来自我的诚信,而非来自我之外的任何外在权威。
因此,“律”就是诚信在书契活动中具体表现,就是诚信,也就是“道”、“道义”。
《周易·师卦》第一爻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意思就是出兵打仗要遵循道义。这是“义兵”、“义战”的起源。其实质也是用中国固有的书契文化去改造和同化外来和后起的战争文化。
现代汉语中“法律”之“律”,“规律”之“律”,完全偏离了“律”字之本意,彻底沦为外在之“律”,成为人必须服从和遵守的外在的权威性的规定,把传统中的参与人基于诚信的共识性因素,把参与人的直接认同、接受和承诺完全剔除了。
在现代的“法律”和“规律”中,其具体条款的权威是来自人的诚信之外的“客观因素”。它们生成无需当事人自身的参与,相对于“客观因素”,当事人自身是不重要的。而“法律”和“规律”条款的具体生成过程中,又表现为一个“学术研究”过程,是由法律和其他各门学科的专家们所主导。
因此,法律和各科的科学专家就成为权威之源头,与宗教时代、宗教社会祭司是权威的源头等同。“客观真理”替代宗教时代的神,成为现代文明新的神。科学家们都是可以发现和接触客观真理的人,如祭司是可以与神接触的人一样。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