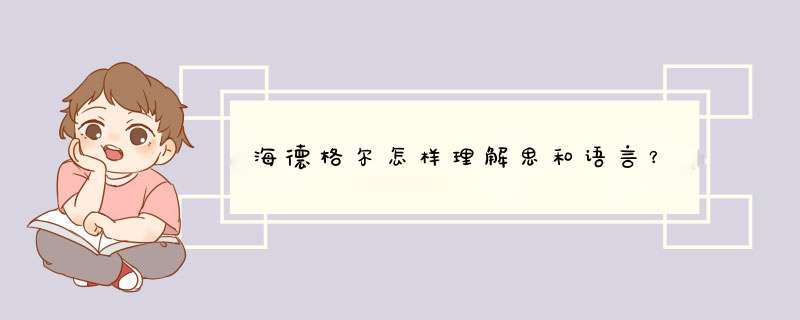
海德格尔思想的路径便是让思纯粹地显示,“哲学的终结”如此,解构存在者如此,重新解释欧洲的历史如此,与尼采的纠缠如此,对赫尔德林的深切通情如此,一再复述诗、言、思的同一也如此。追求思想的纯粹,这既是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以来的思想家的一般特征,也是德国思想家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常深沉之印象的原因。对纯粹思想的不懈追求,极大地突显了德国思想家的美学传统,并将其渲染为一种自觉的风格。黑格尔思想中的“绝对精神”并非是精神追求绝对的对象化运动,而是追求让精神纯粹地显示自己的道路,整部“精神现象学”都在做这么一件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是在探索纯粹思想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由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喜欢将人放到理性所采用的一种形式的位置上考虑,并从对理性的存在性解读中使人获得存在的规定性,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事实上就是对思想的存在性的检讨,是对纯粹思想之可能与不可能的一般条件的检讨。无论黑格尔、康德,还是费希特、谢林都是在稠密的理性包围中酝酿纯粹思想的浪漫主义史诗。它们是人类精神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
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没有脱离这一传统,而且将这一追求纯粹思想的传统烘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就运思的幅度、尺度来说,还是就事实上达到的思想纯粹程度来说,他都远远超出了古典浪漫主义运动(包括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奠基人。他不仅回到了存在的最深处,而且摆脱了思想的形式条件的约束,回到思想的自行道说上来;他不仅使我们终于获得了把整个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审视物来看待(这使以往的各种形而上学体系只能保留其有限的思想价值)的机会,而且他还是把人类在思想上从空间世界转向时间世界的搬道工,并且他还是技术座架将人类发射到行星命运中去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这些非同小可的事实不仅使海德格尔成为世纪事件、千年事件和哲学之为哲学的事件,而且是思想本身的事件,是思想向渊始处返还的事件,是思想在最基本处讲话的事件,是思想将我们的存在性一同显示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事件。
海德格尔思想中蕴藏的巨大的文本力量和对思想者强大的聚集力量都源于海德格尔思想的纯粹,源于让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的喷涌着的深刻让予,让思想在纯粹中自行说话。这种纯粹而又广阔的文本力量是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所不能及的。这因为他们不能例外于哲学家,他们因受蔽于哲学事业而不能献身于纯粹思想的最为虔诚的事业,虔诚地聆听纯粹之思的纯粹天命。
一、
在的开辟底定了思作为事件出现的渊始性。追问在,并使古老的对•存•在•的•追•问变得更具有追问的紧迫感,更值得追问,才能让思自由地返回它的源头。思返回源头之时,也是存在脱落所有遮蔽物而回到在的纯粹之时,澄清有关存在的迷魅隐语是海德格尔追求纯粹思想的事业中一项奠基性的工作。
在海德格尔的语汇中,与追问在有关的语词有四个:Existenz,Sein,Seind,Dasein。Existenz源于拉丁语,指称由复合命题构成的存在,保留了罗马人追求事物的反射性、类比性的基本语境,因此我们在中文中用“存在”称呼它,以示它存入某种东西和某种意义中去的在的复合性质。Sein是古老的德文词,有遣送到什么地方和命系于什么的朴素但也严重的语义。海德格尔以这个古老的德文字作为聚集思想基本语汇力量的场所,并通过它返回古希腊思的源头。我们用中文的“在”翻译它,作为思的同源语保持其渊始的无蔽。Seind是sein的第一分词,在语源上它与Sein具有同源性。但海德格尔赋予这个字的通常意思却是“存在者”的意思,只在少数情况下还它以“在者”的真面目。这里,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遗留了一些混乱。中文翻译应视具体语境的不同或译“存在者”或译“在者”,这里不宜详述。海德格尔用语中虔诚护守Sein的对称语是Dasein,中文按熊伟先生的翻译线索通译“此在”、“定在”或“亲在”,偶尔有人翻成“真在”。“此在”和“定在”取直译,将“Da”和“Sein”的空间联合直摆在中文中,“亲在”和“真在”试图意译,强调它才是真正的存在,但亲在哪里,真在哪里,并不能直接说出来。实际上,Dasein正是海德格尔表示入思的思物,此一思物受到、听到在的召唤,并因与在的深切遭遇而运思在和言说在。经权衡我们给“Dasein”一个朴实但可能恰切的中文翻译,我们将其译成“在者”,以此显示它与Sein在思上的同源性。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在追求纯粹思想——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的同时,也铺了一个思想要通过思者来思想的基本面,Dasein理所当然地被海德格尔用来打通Sein和Existenz的关系,使混迹于日常状态中的复合意义上的对存在的思维(区别于真思想)与受在遣送和受思运规定的在的思之间有某种沟通的可能性。但在的遣送是基础,并因在的遣送和让予才使存在成为存在。如果在的遣送和让予撤回了自己,存在将消失于无迹。在无法从“是或不是”那里得到规定,无论这样的规定多么严密、多么深思熟虑,它都无法与在契合,而是越加远离在。在只能于让予中现身和显示,并于此一让予和现身中绽放思的基痕。
求纯粹思想——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的同时,也铺了一个思想要通过思者来思想的基本面,Dasein理所当然地被海德格尔用来打通Sein和Existenz的关系,使混迹于日常状态中的复合意义上的对存在的思维(区别于真思想)与受在遣送和受思运规定的在的思之间有某种沟通的可能性。但在的遣送是基础,并因在的遣送和让予才使存在成为存在。如果在的遣送和让予撤回了自己,存在将消失于无迹。在无法从“是或不是”那里得到规定,无论这样的规定多么严密、多么深思熟虑,它都无法与在契合,而是越加远离在。在只能于让予中现身和显示,并于此一让予和现身中绽放思的基痕。
这样,海德格尔运思在的基本事情就返回到如下问题:介于我们不断超越和往返的存在者与离开它我们就无从运思的在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介于受形形色色的存在者规定的实在物、导出物的本体论和受在托付的伟大的现实性(真思想的领域)之间的基本关系如何
这里,海德格尔并没有拘泥于语词的纠缠,而是区分出基本的东西和次一级的东西。攸关在的伟大现实性的思想不得不源出于在的东西,海德格尔将其聚拢在ontisch这个词的名下。受存在摆布、被存在 夺、往返于各个层面形形色色的存在者之间的实在物和导出物,海德格尔将其归纳于Ontologie这个词的名下。ontisch,我们权翻作“在性的”,它前承古希腊语的physisch(绽放、涌现、现形,在聚集中显现),后接德语的Sein(在),我们得以运思的一切原始条件,思想在任何条件下运思的伴随物。Ontologie,我们将其翻成“存在学”。这个词概括了以逻辑(逻辑化的逻各斯)的方式规定和解释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它在阻截了逻各斯道说上的直陈式力量之后,使在丧失了自在的•涌•现,而必须按照逻辑的形式条件来•表•达。这个转变不仅完成了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变,而且使思想全面地卷入先验、经验和超验的概念循环,即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者之间无休止的纠缠。不仅此一存在者从另一存在者导出,而且导出的依据和解释也出于同一面孔的第三个存在者,这种导出导入的存在学逻辑为“上帝”、“第一推动力”、“终极原因”和各种各样的“原理”提供了充足的逻辑担保,尽管这种逻辑担保恰以牺牲对思想渊源的返还为代价。对这样的存在者的问与答,从根本上说没有实质意义,只是卖弄不着边际的学问而已,因为每一个这样的存在者在进入发问前都已预先被其他的存在者所规定,每一种这样的规定都不过是来自于存在学的某种存在观点而已,虽然看上去新面孔反复出现并且言之有据,但与纯粹的思沾不上任何关系。
是于存在者中物色“上帝”、“世界”、“人”这些终端命题,还是于返还在的途中耕耘那使在借以道出自己的基本语汇的力量是安于存在者游戏的逻辑分殊,还是让我们踏上在的遣送之路是在存在者的家谱中不断加上新的存在者名字,还是迎向事物的风,让思经受在的考验是倡导沉溺于思考的对象化研究,还是学会面对思的事情是让古希腊思想家(在的敞开者)继续流于学术研究的对象,还是让他们作为思的见证者卷入到我们当下思境的筹划中所有这些显示道路、决心和思想面貌的分际均已蕴含在“存在学”和“在性的”分际中。而在海德格尔之前根本就谈不上这样的分际,不过是此一形而上学反对彼一形而上学而已,而这些相互反对的形而上学却都立基于同一个存在者平面上。
解构存在者并不是海德格尔思想内首要之事,而是恢复在的道说力量时附带产生的工作。他在惊愕地发现返回在的道路只能是由在而来的道路时(Kehre,转向),才自觉地关注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几乎一次性地将在耗罄而流于平庸的存在者,并由此从根本上毁弃了由physisch绽放的在的光芒。因此,重新解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差不多伴随着海德格尔一生的思想活动,这种返乡之旅,这种重逢历史的惊讶,这种让在屡获绽放之光的思的闪烁使海德格尔对在的追问越加纯粹,几乎完全达到了在、思、言、诗的同一让予。
在的真理是什么远思的诗是在的地形学,本真的思是在的事件,思的感念让在出场说话,在的说聚集为话语,话语才作为解读的语言出现在词汇里,保护在者借以道出自己的基本语汇的道说力量,才成其为思者不多也不少的本真的赤贫,这原朴的赤贫才让紧守住自己的已发生的事情绽出。这样事实才能显示自己为事实,才使真理发出自己的本然之光。否则,真理仍一如既往地被押解在存在者的循环往复中,使其徒劳地挣扎于所谓认识与事实的符合中。但对真正的思者来说,物是自体性的,如果物不显示自己,事实就不成其为事实。事实在物的显示中才获得事实的思想性,欲使认识及作为认识条件的命题对事实有所作为,必须尊重事实显示为事实这一原初局面。事实显示为事实这个无声的静谧世界才是思者真正的基地。这个基地乃那些抵达了在的真理的思者的家,他们都是在的事业的自觉的守护者,而不是骄狂的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的主人。这就从根本上解构了在存在者意义上繁衍的、令人厌恶的、喋喋不休的主客体游戏的虚妄。因此,解构存在者并不是思者的真正目标,而是思者向在的真理返回时使存在者自行脱落。凡不能显示自己为事实的一切所谓事实都将在思者对在等深的耕耘中自行枯萎和脱落,在的地形地貌才如水落而石出。只要哲学保持在柏拉图主义的纲领中,保持在形而上学的存在者的逻辑分延中,它就不是思者的栖居之地,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思者解构的东西。因此,海德格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虔诚的思者,是思园的守护人,是思路的养路工,他的意义不在任何形而上学体系的掌握和评价之中,他的意义显示在在、思、言、诗的同一让予中,显示在在的地平线的原朴的开辟中,他是由在开辟而由存在转释的西方文明导致的带有宿命性质的人类天命的知情人和无奈的深情关注者。这是在存在道路的深深挤压中抛出来的思者,他必须以纯粹思的姿态完成对存在的对抛,在纯粹的思中迎向事物的风。
我们说思,不说思维、思想和思考,这是由海德格尔自身的文本决定的,并不是刻意追求中文的简洁和故弄玄虚。如说思维,那定在某一确定的维度中运思,这种确定的维度,在西方就是在形而上学中思想,就是周转于各种存在者中间,这必将掩盖海德格尔运思的光芒,使海德格尔流于平庸的形而上学家。如说思想,则漫无边际,任何一种存在者层面的矫情卖弄都可能被标榜为思想,虽然并没有真正的思想事情的发生,没有让思想思想着思想本身。如说思考或反思之类,则能搞出很多热闹场面,容易摆出严谨的做学问的架势,纠缠于各种逻辑相关项,忙于构造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是通过存在者延伸存在者,或用此一存在者反对彼一存在者,这个存在者取消那个存在者,虽然这里面会折射出一些所谓“时代精神”,但与思的事情本身无关,虽然观点芸芸,甚至不乏深刻之见,但思并没有露面。因此,海德格尔才孤寂地提示说,几乎无人知晓做学问与思的事情的不同。
“只有我们自己思时,我们才能到达叫作思的东西。为使此一思的尝试不至归于不幸,我们必须愿意学习思。一旦我们乐于学习,那就已经承认,我们尚不能思。”3思的困难在于我们还不会思,不会思的根由在于我们习惯于思维,习惯于在存在者之内思维的安逸,不必经受思风的凛冽。人们久已不会思了,要学习思实际上要从头学习,回到前哲学、前形而上学。这样的学就不能照着哲学的规定学,不能照着形而上学的样子学,不能以存在者的样子模仿存在者。学习思意味着把思放行到源头中,使思重获绽放之可能,使思向它的本真处聚集,靠拢向自行在本质中允诺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种思的下沉的艺术。学习思即是创造让思在源头活跃的条件。“确有某物,它自身出于本然,仿佛从源头涌来,让我们入思。确有某物,向我们娓娓倾吐,让我们牵绕于它,让我们在思的状态中迎向它:这就是思。”4问题在于谁的惊愕能深究它。“我们还没有入思,这决非只在于人类尚没有充分地向那在源头上就是有待去思的东西靠拢,因为这有待去思的东西本质上还保留着让思的状态。我们还没有入思的根由更主要地在于,这一让思状态自身已背人类而去,早已背人类而去。”早已背人类而去,早在何时它不以时间计载,而是于在转成存在、在者转成存在者之时,自此,思就不处在让思状态,这是存在者意义上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向其靠拢的。让思状态是让思者在思中远思,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是根本上有别于精确思维的严格的思,是思与让思的绝对合辙。
在海德格尔之前也有不乏深刻的思想家,他们也感到了科学思维与真正的思想的不同,他们也尝试过在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那里验证自己的判断,他们最终发现,这一可悲事件的发生其罪魁祸首是逻各斯对密托思(Mythos,通译“神话”,中文的这个翻译过于单薄,不足以表达Mythos的真髓,故与“逻各斯”一样改成“密托思”这个音译)的破坏,逻各斯取代了密托思,逻辑又支配了逻各斯,统计学又取缔了逻辑,最终导致思想成为经验科学。这个貌似清晰的在存在者中几经更替的解释以逻各斯与密托思的对立为前提,完全漠视了思与在的同源性,漠视了思的让思状态以及与此状态对应的思的自行隐退。思作为在性的思完全没有像在概念中替代那么容易。“密托思是规定一切人的本质并攸关人的根基的律令,此一律令让思敞开在显示中,敞开在出场中。逻各斯言说的(与密托思)是同一个东西,并非如传统哲学史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密托思与逻各斯对立起来,才使哲学脱颖而出。相反,恰恰是早期希腊思想家(巴万尼德,残篇第)在同一个语义上使用密托思和逻各斯;只是到了无论密托思还是逻各斯都不能固守其渊始本义时,密托思和逻各斯才开始分开,并对立起来。这件事在柏拉图那里就发生了。密托思惨遭逻各斯破坏这种看法,是历史学和哲学中的近代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主义的根基中继承过来的一个偏见。(同样,)宗教从来都没有被逻辑破坏过,事实总是并只是:神自行隐退了。”
海德格尔思中的神始终是密托思意义上的神,而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神。这种神的自行隐退实际上就是密托思和逻各斯的同步退场。密托斯和逻各斯的同步退场的直接结果是,在转化为存在,思转化为思维,言说转化为语言,从在、思、言的同一和纯粹转化为存在、思维、语言的形而上学规定物,并进而在形而上学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存在科学、思维科学和语言科学观点,并大兴主体——客体的思维风气,由此用学问的对象取缔了思物。海德格尔给思提出的任务便是恢复思在源头说话的能力,让思重新于在中得到吩咐,这样思才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哲学形而上学的纠缠,让尾随着我们思中古之又古者在思风的鼓荡下横跃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如沐春风,心中有物,眼前有物,而不是重重叠叠的存在者对象。海德格尔以充分的思的经验断定,只要懂得思的源头,我们就会勇敢地从哲学抽身,投入对在的思中。
从哲学抽身,投入对在的思,思在的地形地貌,让在的地形地貌显示在思中,让在自行开辟于如花绽开的语词中,使思的事业兴旺起来。纯粹的思,对海德格尔来说,那就是让思摆脱存在者,让思返回在,让思永远迎着物的风寥寥缓行。用几句话说出海德格尔对纯粹的思的耕耘并不难,但要在思的事业中增加几分纯粹谈何容易,这不仅需要回到思的原初局面的能力,而且需要对思的事业的虔诚;不仅需要打碎复合语境中的存在,而且要安顿好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位置;不仅要让一位本以哲学为终身事业的思者最终宣布哲学为虚妄,而且还要痛苦地宣布哲学对思的事业的根本损害;不仅要费尽心思地重回欧洲历史的源头,而且要从根本上解构西方文明赖以发端的欧洲哲学史,并最终察觉哲学已终结于以技术座架为基础的近代世界以及与近代世界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哲学沦落为经验科学,实际上是被经验科学所取代,它就是哲学的终结本身,它被一种更具宿命性质的技术座架所取代,这种技术座架既不能为经验科学所理解,也不能被哲学传统挽回,它正在一个巨大的思想真空中无声地安排着人类的命运。从地球的范围看,技术座架开始了一个世界文明时代,它的基础是以西欧思想为基础的近代化。若把思想移居到地球以外的角度看,技术座架打开了一个不祥的行星语言的时代,它的基础同样是以西欧思想为基础的近代化。在此一近代化进程中,不是科学引导技术,而是技术座架规定着作为 *** 纵人类劳作可能的计划和安排之理论的科学,被人类标榜成科学成就的人造世界不过是技术座架提供给人类的一个过渡的简易居处,它最终把人类流放到哪里,在海德格尔看来还无人知晓。但对技术座架规定着现代自然科学的本质,以及这种规定所必然得到的直接后果,海德格尔则早已在思中料定:“在可见的未来,人类将被摆到可•制•作的位置上,就是说,人们需要什么就能纯粹在有机体中构造出什么:精干的抑或笨手笨脚的,机灵鬼抑或傻子。离这一天已经不远了!”这句话是海德格尔在1969年接受采访时说的,距今不过三十多年。当年思者焦虑不安的预感已是今天思维者当作炫耀的现实,又有哪个思维者懂得得意洋洋背后的凶险呢
思者如海德格尔,对由形而上学造成的欧洲内在虚无的历史来说,他迟到了三千年;思者如海德格尔,对技术座架悄然安排的人类宿命来说,他又早生了一千年。海德格尔在引证H•V•克莱斯特的话时,已经道出了此一悲凉心境:“未及他来,我便辞他而去,先他千百年,我已听命于他的精神。”8海德格尔在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时用对神的期待来表衷这一精神,凄苦地承认还只有一个神能救渡我们。我们这些几百年来一直受思维精确性诱导的人,自以为是思的主人,完全不知思物为何物,习惯了用思维制作存在,既听不懂海德格尔对“精确的思维”和“严格的思”的区分,也听不懂科学不思的深长意味。科学无法以科学的自在性给出科学是什么,它必须在哲学运思的这一维中被证明,科学自己完全不知道真正有待去思的东西是什么,从含有自省能力的完备理性来审视,科学实际上最缺理性这一维,它完全是个知性的产物。它首先不知道它的语感力量从哲学而来,其次不知道作为它的基础的哲学已自行终结,再次更不知道它已是受技术座架驱使的在制作的延伸中无目的扩散的东西。危险更在于,层出不穷的思维者至今尚不知这种无目的扩散的严重性。这注定了人们听不懂思者的话语,人们继续满足于用思维制作存在,而不是让思为在的出场创造条件; 人们继续梦想做思的主人,而不是受思的召唤虔诚地做思的仆人,这一麻木的现实使海德格尔以神、精神、在、思、言、艺术等名义开启的纯粹的思的光芒湮灭于无迹。但对思者来说,耕耘思之纯粹,听思对在的回响是他唯一的事业,因为它是思想话语的原初。但作为林中路的知情人,他没有忘记对那些有可能入思的思想者提示一句:“只有当我们经验到几个世纪以来辉煌的理性实是思的劲敌时,思才真正开始。”
语言,言语,说,在海德格尔追求言说的纯粹中,我们会碰到这三种容易混淆的语境。在德文中分别为dieSprache,sprechen,Sagen。dieSprache是动词sprechen的过去时的名词化,指某种语言观中的语言,某种句法关系中有使用价值的语言,人们通常说的工具意义上的语言,我们用中文的“语言”对应它。海德格尔用sprechen去抵消“语言”的本意是让语言自行言说,不是通过某种语言观(存在者)形成表达意义上的语言,我们用中文的“言语”对应它,以示语言自己说,不作为人的工具意义上的语言来表达什么人的主体化意图。Sagen,这是一个古老的德文词,海德格尔对这个词给予的思的期望最多、最纯粹。这个词的德文语境与密托思的希腊语境最切近,于在的开辟中说,在显现中说,借神意传达、启示地说。它既不因为什么而说什么,也不为了什么而说什么,而sprechen则总不能在句法中摆脱关于什么的说、围绕着一个什么对象来说的阴影。因此,从纯粹性上考虑,海德格尔更倾向于让Sagen在思中说话,我们用中文的“说”对应它,以示既不为什么而说,也不因什么而说,而是说说着,就像海德格尔的思的纯粹处在于,他不是关于什么的思,而是思本身一样。这是海德格尔思的文本力量所在,说的魅力所在。
海德格尔的言路从出于诗、思、在的同源性。纯粹的在、纯粹的思和纯粹的言之所以可能,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得益于这一同源性。要获得这一同源性的洞见,关键看思者能否向思的纯粹处奋力返还,返还到思思想着思本身的纯静之处、单纯之处,向思的寂静处聚集,聚集在思的最基本处,唤起思的最基本词汇的力量。在这样的思的差——异中,在进入说,说的涌现和绽放聚集成语言,此一语言本身就是在的栖身之家,人就住在这样的家里面,此一渊始于纯粹的家里面住着纯粹的思者,他们或许是运远思之诗的诗人,或许是踏进思的分延进程中的艺术家,或许是在话语中对峙、狱炼、经受分延的冷酷考验的语言骑士,这些思者都是这个家的护家人,他们都虔诚地守护着在借以道说自己的最基本词汇的力量。
这是一个佛门对联,自,自我。 在,存在,存在的实在。 观,不动心念,静静地注视着;集中精力,目不转睛、无私无欲、无思无虑的看着。 如来,生命的本真状态。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原本如此。 见,看到。
意思是: 自我的存在,要靠存在的自我来观察;只有存在的自我,才能观察自我的存在。 生命的(原)本真(实)状态,要在好像看,又好像没看的(超越了看与不看)时候,才能看得到;只有超越了看与不看,进入了似看非看,非不看的无我状态,才能看到生命最原本真实的状态。
在这里,不是用肉眼,而是用心灵的眼睛(自我的内视功能),静静地、注视着、肯定着客观存在的自我(自我非我,无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在——实相,无形无相,非色非空)。有想看的意愿,看不到;没有看的意愿,根本不可能看到。
只有升起看的意愿,然后把这个意愿放下(不是放弃,而是不执著于看),在一种似看非看,非看,非不看;不看而看,看而不看,超越看与不看的状态,才能观察得到生命我最本真的状态——如来。
客观存在的自我,不在体内,也不在体外。向外求,找不到,向内求,没有,它在生命的深处。无内无外,超越内外;非色非空,超越色空;无人无我,超越人我。
庐陵何绍先在《对联汇海》中说:“考古家谓对联即桃符遗制,始于蜀孟昶而盛于明孝陵(按即朱元璋),不知此指门联而言。若堂室之题句,则诸葛武侯之‘淡泊以明志’,孔北海之‘座上客常满’,已为滥觞。”
何绍先认为,孟昶题联只是门联(亦春联)之始,而非整个对联之始,这是不错的。但他把对联之始推至汉末,又未免早了一些。因为在律诗尚未形成之前,即算象孔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这样对得很工的句子,也只能算一般对偶。
而今的所谓“对联”,当出自唐代,不会迟于晚唐。因为在初唐与盛唐之际,律诗已完全定型,不管是五律还是七律,都要求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为求对仗工整,还有一整套规矩。这就为对联的出现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由诗的对仗发展为对联,当是从摘句开始的。六朝时就有从一篇作品中将精彩的句子摘出加以评论的情形,锺嵘的《诗品》就是代表。但当时还并非只摘对句。律诗臻于完美,佳对日出,专摘对句的情形,就日益增多。
这对对联在唐代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个促进。再和美妙的书法相结合,对联也就开始放射出异样的光彩。至于专摘对句的书籍,据说隋末就有了。传杜公瞻曾奉隋炀帝之敕撰进过《编珠》四卷,但隋志、唐志均未载,至宋志始著录,而宋人未见引用亦无旧刻旧钞流传于世,而今只能从清康熙年间高士奇家刊本,得见其大致面目。
据高氏所称,此书得于宫廷内库废纸堆中,但“世颇疑其依托”(梁章钜《巧对录》)。此书若实有,对对联在唐代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唐人又喜欢书壁。李白()《草书歌行》说怀素写字时:“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
陈彬龢《中国文字与书法》亦云:“(唐)文宗尝于夏日集学士联句,命(柳)公权题于殿壁,字径五寸。”此事《新唐书·柳公权传》有载。而唐人在写诗时,有的将先得的一个佳句写在纸上或者壁上,慢慢求对,对上了就配上去,在今天看来,这就等于在做对联。
参考资料:
最经典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林中路》,都很难懂。
如果是要入门水平的,那往往不是经典。可以去看看知名高校出的《哲学通论》孙正聿、《哲学概论》一类的书。推荐复旦王德峰的《哲学导论》。
另外推荐
文德尔班(Windelband, W):《哲学史教程》(1-2卷
罗素(Russel, B):《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上、下),
施太格缪勒(Stegmueller, W):《当代哲学主流》(上、下
希尔贝克(Skirbekk, G):《哲学史》,正在翻译中,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
汪子嵩主编:《希腊哲学史》(1-4卷),人民出版社,1997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
陈修斋:《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民出版社,1986※
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赵修义、童世骏:《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99
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穆尼茨(Munitz, M K):《当代分析哲学》,吴牟人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王路:《走进分析哲学》,三联书店,1999※
潘德荣:《诠释学导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
考夫曼(Kaufmann, W)编著:《存在主义—从陀斯陀也夫斯基到沙特》,陈鼓应、孟祥森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商务印书馆,1981※、1982※;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共5本:《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
陈启伟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俞吾金、吴晓明主编:《20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共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经典著作(A)
柏拉图(Plato):《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余灵灵,罗林平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
奥古斯丁(Augustinus, Aurelius):《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
笛卡尔(Descartes, R):《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培根(Bacon, F):《新工具论》,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
洛克(Locke, J):《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
休谟(Hume, D):《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 馆,1981※
斯宾诺莎(Spinoza, B):《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6※
卢梭(Rousseau, J):《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96※□◎
康德(Kant, I):《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历史理性批判》,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
费希特(Fichte, J G):《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97※
黑格尔(Hegel, G W F):《小逻辑》,贺麟,商务印书馆,1980※□;
《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美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的序言和导论※
费尔巴哈(Feuerbach, L A):《宗教的本质》,人民出版社,1999年※
马克思(Marx, K):《***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 199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 , 1962※
恩格斯(Engels, F):《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 1997※
普列汉诺夫(Plekhanov, G V):《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真译,三联书店, 1965※
孔德(Comte, A):《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 , 1996※
穆勒(Mill, J S):《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 1959※
斯宾塞(Spencer, H):《社会学研究》,张宏晖, 胡江波译,华夏出版社 , 2001
尼采(Nietzsche, F):《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 2001※
赫胥黎(Huxley, T H):《进化论与伦理学》,《进化论与论理学》翻译组译,科学出版社,1971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Bergson, H),刘放桐译,商务印书馆,1963
詹姆斯:《实用主义》(James, W),陈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
杜威(Dewy, J):《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89※□
罗素(Russell, B):《哲学问题》,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9※□;
《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卡尔纳普(Carnap, R):《哲学和逻辑句法》,傅季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 1996※◎
波普尔(Popper, K):《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
《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纪树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库恩(Kuhn, T):《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胡塞尔(Husserl, E):《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 1999;
《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86※
海德格尔(Heidegger, M):《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 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1996
萨特(Sartre, J):《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雅斯贝斯(Jaspers, K):《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伽达默尔(Gadamer, H-G):《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罗尔斯(Rawls, J):《正义论》(第1章),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哈贝马斯(Habermas, J):《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 1989※
罗蒂(Rorty, R):《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