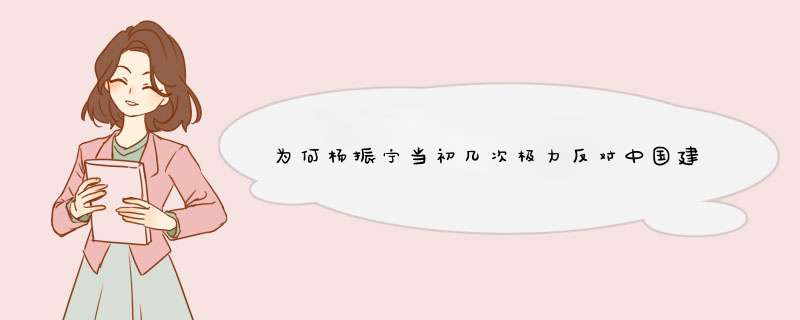
中国目前应不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围绕这个问题,物理学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物理学界分为两种观点,王贻芳力挺建造大型对撞机,认为这是中国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一旦成功将会改变未来,而且这个设施可以吸引更多国外优秀人才,有利于提高中国基础科学的地位。
而杨振宁先生则认为,中国没必要建造这个昂贵的东西,而且结果还是未知,应该把钱用在其他高回报的科研领域。
这个巨大的圆圈就是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
美国也曾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SSC),花费30多亿美元都没建造好,最终不了了之。2008年欧洲花费100亿美元也建成了一个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这是一个27公里的圆型隧道,位于地下100米,是人类目前造出的最大装置。
隧道内部
造这么大一个圆圈,就是为了让“粒子”在这个超长距离圆管道里加速,一直加速到接近光速的99.9999991%!然后两个“粒子”在这个速度下相撞。物理学家期待能够撞出某些新物质。可惜欧洲实验了那么多年,也没有撞出想要的东西。
没有人能知道对撞机到底能撞出什么东西,或许永远也撞不出东西。所以,杨振宁的观点并没有错,毕竟360亿人民币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1983年7月,美国打算全力建造一个“世界最大”的加速。资深物理学家戴维·杰克逊将它命名为“超导超级对撞机”。1986年完成了雄心勃勃的工程方案:环形粒子加速周长87.1公里,隧道位于地下70米,8662块超导偶极磁铁用10个冷冻厂的液态氦维持在4.3K低温,接近光速的两束质子在4厘米孔径中以40万亿电子伏特能量迎头相撞,模拟出宇宙大爆炸后瞬间的物理环境,找到希格斯玻色子和其他新粒子。预计总成本44亿美元。
德克萨斯超导超级对撞机工程开挖的隧道和竖井
然而随着工程造价太高并不断攀升。1989年预算为59亿美元,1991年达82.5亿美元。引起了美国史上最大的一次争议,那就是建造这个有什么用,耗费如此大的资金。
最终,1993年,国会众议院以280票对150票的悬殊比例通过决议,将总预算已增至110亿的超导超级对撞机“就地正法”。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废墟”
360亿的投资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一笔巨资,另外中国目前还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医疗、教育以及养老等领域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另外一点,也不得不说,这一项目要顺利进行,预计将有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为外国科学家,杨振宁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为别人做了嫁衣。
杨振宁是物理界少有的大量运用数学的科学家。
他曾经说过: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堪称奇迹中的奇迹的是,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杨振宁提出要“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就是用数学来研究物理。
1983年,杨振宁向中学生介绍自己的学习过程时,就专门提到了一个人。
他说:“有一位刘薰宇先生,他是位数学家,写过许多通俗易懂和极其有趣的数学方面的文章。我记得,我读了他写的关于一个智力测验的文章,才知道排列和奇偶排列这些极为重要的数学概念。”
在对一种叫做“激子”的微小而短暂的物体的本质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 探索 之后,研究人员终于成功地对其结构进行了成像,揭示了电子的真实位置。这些发现最终可能会“帮助物理学家创造新的物质状态或新的量子技术。
“激子”出现在半导体和绝缘体等其他材料中。当半导体吸收光子或光粒子时,它会导致电子跃迁到更高的能级,在其位置上留下带正电的空穴。电子和空穴相互环绕,形成一个“激子” —— 本质上是电子和空穴的整个区域。因为,电子带负电荷而空穴带正电荷,所以激子本身是中性的。但激子是短暂的,因为电子几乎总是突然回到它们的洞中。当电子落回内部时,它们会发射出一个光子。
主持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大约在90年前,科学家们首次发现了激子。但直到最近,人们通常只能看到激子的光学特征。例如,当激子熄灭时发出的光。它们性质的其他方面,比如它们的动量,以及电子和空穴如何相互绕转,就只能从理论上描述了。”
因为电子同时扮演粒子和波的角色,它们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被确定。一个激子的“概率云”(它所构成的影响范围)是电子可能位于空穴周围的最佳指示器。
研究人员试图绘制激子的波函数,这将能直接定义结构的形状和大小。他们描述了一种探测激子动量的方法。在今天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杂志上的最新研究中,该团队用激光照射半导体,催化光子的吸收。这个半导体非常薄,是一种只有几个原子厚的二维物质薄片。
当激子形成后,研究小组用高能光子将它们分解,将电子轰走。 他们用电子显微镜绘制电子出口的地图。
上图:激子的平方波函数。
这是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去年12月,他们发表了一种直接观测电子动量的方法。该技术使用一种名为钨二硒化物的二维半导体材料,放置在一个温度为90开尔文(-183.15摄氏度,或-297.67华氏度)的真空室内。这个温度需要保持,以防止激子过热。
激光脉冲在这种材料中产生激子。然后,第二束超高能量激光将电子完全踢出,进入由电子显微镜监控的真空室。仪器测量电子的速度和轨迹,这些信息可以用来计算出粒子在被踢出激子时的初始轨道。
科学家表示:“这项技术与高能物理的对撞机实验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对撞机实验中,粒子以巨大的能量被撞在一起,使它们断裂。在这里,我们正在做一些类似的事情,我们使用极端紫外光光子来分离激子,并测量电子的轨迹来描绘里面的东西。”
通过测量电子离开半导体的方式,研究人员可以将激子的位置、形状和大小拼合在一起。本文顶部的图像,看起来有点像晴朗天空中的太阳,但它描绘的是激子的概率云。换句话说,就是电子最有可能绕着它留下的洞飞来飞去的空间。
主持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解释道:“这项工作是该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当粒子形成更大的复合粒子时,能够可视化粒子的内部轨道,可以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了解、测量和最终控制复合粒子。这可以让我们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物质量子态和技术。”
自1931年第一次预测激子以来,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人类已经更接近于描述亚原子结构是如何实际表现出来的。这次最新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些量子力学有了更全面的理解,相信当激子达到百年诞辰时,肯定会有更多、更广阔的的研究发展起来。
如果朋友们喜欢,敬请关注“知新了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