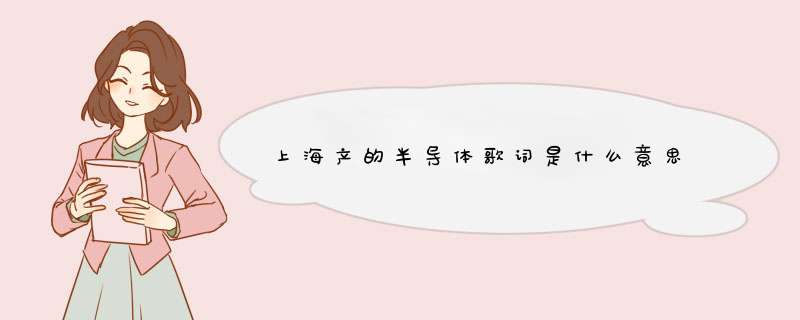
1976年7月28日凌晨1时许,我拖着劳作了10多个小时的疲惫之躯,从唐山范各庄煤矿300米深的井下回到了地面。突出的感觉就是热,而且无风。
洗澡、吃饭然后回到位于四层楼的集体宿舍。邻室的天津知青张新伟闻声而来,我忍着困倦、坐在床上和他下了一盘象棋,眼皮就睁不开了。张新伟问:“服不服输?”我说:“服了。”即躺倒昏昏睡去…… 没睡多久,就觉得床拼命在摇。初始我以为谁又闹着要跟我下棋,但很快就发现不对,床不仅在晃,而且上下颠簸。
没有这么闹的!
朦胧中,我以矿工遇险时特有的敏捷,从邻窗的床上一跃而窜至门口,黑暗中似乎听到同室的北京知青小王喊了我一声。
我扶着门框,勉强站住,却再迈不开一步,只觉得门在晃动、楼在颤抖,耳边是闻所未闻的地声,身后窗外是迅速闪现的地光……大难突然而至,仿佛世界的末日来临。
我几次险些被摔倒,多亏我在井下干了一年回柱工,练就了逾百斤膂力的手臂,死死地抓住门框。我不能倒下,煤矿的安全常识告诉我,倒下受力的面积更大、更危险。
许多的墙皮、砖头等杂物落在我身上,我觉不出疼痛,但却恐怖之极,头发根根竖起,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是条件反射般地意识到:门上边是碹,相对结实……
恐怖在迅速升级,考验着人的神经——前后摇、左右晃、上下颤,无规律地簸……脚下是大地的舞蹈,它疯狂地释放着多年沉睡而积聚的能量。
我想喊,喊不出;我想走,走不了;欲笑不能,欲哭无泪;忍无可忍又躲无可躲……就在神经快要崩溃之际,晃动突然停了。
周围瞬时像死了地一般寂静,继而传来了慌乱的人声。惊魂稍定的我,迅速恢复了四级矿工遇险时应有的冷静。凭借矿工的夜视能力,我看到楼道已严重扭曲变形 ,楼板倾斜欲坠,部分外墙坍塌……
我取下晾在门内铁丝上的一套的确良衣裤,这是我头天新洗的,抖了抖上面的土,迅速地穿上。在黑暗中,摸索着下楼。有人在说:“地震了,轻点!”似乎是怕脚步重了震垮了楼梯。
我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但小腿还是磕了个包,这在当时已经不算伤了。终于走出了楼门,提着的心才放下来。幸亏范各庄矿的宿舍楼是新盖的,结实,否则垮塌下来我们就都被活埋了。
院墙已经全部倒塌,一二三层先出来的人们聚集在马路上,议论纷纷。我忽然发现自己很特殊,大家多是只穿三角裤,只有我衣裤齐穿!
张新伟很快就发现了我,晃着一身白肉嚷嚷着向我走来:“立立,服不服?这回全服了!”
旁边有人随声附和:“就是,那么多七级工、八级工,这么大的窑势(矿工用语:地下的情况)楞都没看出来!”
我突然想起要马上救援,赶紧问周围的人:“有没有受伤的,楼里还有没出来的吗?”
年轻矿工天性乐观,马上有人回应:就你出来的晚,地震了还顾穿衣服!
我一想也是,附近几栋宿舍楼幸未垮塌,损毁最厉害的也只是外墙翻塌,且楼内住的都是经过严格体检招来的高中生和插队知青,虽不能说个个身手矫健,但人人年轻敏捷而且都受过正规的煤矿安全教育,遇险时冷静和自救、互救应该没问题。
这时还不到凌晨4点,大地的余震还在不断袭扰着我们。我环顾四周,见大门口锅炉房无人,便突然意识到:如此大震,必然断水停电……我迅速走过去,摸摸锅炉水温尚可,便对着水龙头痛饮。啊,从来没这么拼命地喝过水,下一次,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喝到干净的开水!我一边喝一边想,下一步该干什么?只几分钟,我便喝得肚子发胀,再也咽不下去了,之后20多个小时,我就没想水喝。 离开锅炉房,我到附近的工友家里转了一圈。范各庄矿的家属宿舍多是平房,而且很结实,大都没塌。但更主要的是这里距市中心有30多公里,且在城东,否则也难幸免屋毁人亡。
采煤一区的赵玉山,是我在井下的搭档,他家兄弟姐妹多,已然在屋外开始搭棚子。赵玉山对我说:把你的箱子放在我这儿,省得找不着了……
离开赵家,我返回单身宿舍楼前,此时已是上午。余震每隔二三十分钟便袭扰一次,但大家已由初始的惊慌变为见怪不怪了。
人们互相打听震中在哪里?路上不断有伤员运来,都是矿区周围的村民,一个个灰头土脸,显然是刚从废墟中扒出来。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四面八方都是房倒屋塌,哀声一片!
更让人揪心的是:300米深的井下,还有数千名夜班矿工,地震导致的断电,必使抽水机和升井电梯停运,迅速涌出的地下水,能充满空间有限的井下巷道,把会游泳的人也淹死!
年轻的矿工们滞留在楼前路旁,身后是一片旷野和积水几乎望不到边的塌陷坑。有人在互相开玩笑:去澡堂子看看吧,那儿出来的全是“浪里白条”。但更多的人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我们不知震中在哪儿!不知亲人、朋友的安危!有人到处寻找半导体收音机,希望得到相关的消息,但没有结果。
就在茫然之际,路上出现了一些“黑人”,反应快的高喊:井下的人上来了!
我们围上去打听消息,原来地下震动远不如楼上剧烈,且每根承重30吨的一排排钢梁铁柱,有效地避免了大面积塌方,人员受伤的不多。井下七八级工比比皆是,这些几十年的老矿工对井下迷宫般的巷道了如指掌,且个个具有大将风度,身经百险,刚毅冷静!
虽然停电使装有升降罐笼的竖井无法运人,但通风用的斜井仍然畅通。老矿工带着年轻的矿工们,大家互相招呼着、帮扶着,趟着水,从各个工作面陆续撤出,在井下走了几十里,从风井口回到了地面!
临近中午,天下起雨来,人们无处可躲。路边有个高大的自行车棚,3米多高的棚柱早已震垮,只剩下三角形的棚顶落在地上,中间有约1米的空间。我们蹲在车棚下面,盼着雨停。
雨雾中,路上走来了两个艰难的身影,走近发现,是我班上的工友果师傅,背着他16岁的儿子。果师傅有60岁了,背都驼了,他儿子在矿上的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双腿!
我一拳砸在自己头上:真粗心,怎么没想到医院的危楼里还有人爬不出来!
我快步冲进雨中,把果师傅的儿子放到我的背上。“走,我送你们回家。”
果师傅本就沉默寡言,此时更累得说不出话来。倒是他儿子嘴很甜,大哥长大哥短地说着好听的。我不断地应答着,心里酸酸的:这兄弟没了腿,好可怜!
雨中前行,走了好远,20刚出头的我背着个半截人倒不觉得累,只是果师傅跟不上步了。
果师傅的“家”只是一领炕席几根木棍支起的小窝棚,里面坐着七八个人。见我们来了,她们说的第一句话竟是“里边坐不下了!”
我听说过嫌弃伤病亲人的事情,但亲眼目睹还是第一次;本想发脾气,但见棚里老的老、小的小,壮年的只是妇女,只好压下;让大家往里挤一挤,把那个可怜的小伙子放在了席棚里边……
下午,雨停了,我找到了李君,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长我一岁,我们都是北京长大,又在遵化县插队,而家则搬到了天津。
这时候传来了确切的消息:唐山市区平了!房屋全塌了!地震的烈度更甚于东矿区!
可以确定,震中的方向在西边。我和李君顿时紧张起来,那么天津呢,是不是震得更厉害?我们的亲人怎么样了?
我们决定,明日凌晨出发赴天津,虽然路损、桥断,走,也要去看望亲人。今夜要做好准备工作。
不知何时,家在唐山市内的知青矿工,个个都没了踪影,他们可能回家了。只有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的知青矿工,回家的行动慢了一步。
一天没吃东西了,我和李君到矿工食堂找吃的。食堂已是断壁残垣,能容纳几百人就餐的饭厅一塌到底。
我们每人找了十几个玉米面饽饽,300里的回津之路,就靠它们维持体力了!
下午7时许,一场仅次于主震的大余震突然爆发,席地而坐的人们被惊得跳了起来,几十米外的一座三层楼轰然倒塌,变成了一个大土堆,烟尘冲天而起,是楼高的数倍!
惨烈入目,令人不寒而栗。
夜幕降临了,我们蜷缩在不足一米高的自行车棚架下边,忍受着蚊虫叮咬,棚外是凄风苦雨。我们一夜难眠…… 次日,天刚蒙蒙亮,我和李君便出发了。路过矿医院门前,只见足球场大的空地上,到处是伤员和横尸。一个女孩突然嘶声哭喊:“爸爸呀,你就这么死了!让大雨浇了一夜呀!”顿时,哭声在广场上此伏彼起。
李君显然比我更受不了这悲惨情景,使劲拉着我快步离开。
在矿区外的公路上,我和李君飞身扒上了一辆卡车。特殊时期,司机也没硬逼我们下车。我们在井下经常扒煤车,地面上的卡车,只要速度不太快,抓着车厢后角我们就能上去。
车向唐山驶去,一路上看不到完整的房屋,我和李君心情沉重,默默无语。
车行至唐山市东南处的吉祥桥,纵贯唐山市区东部的陡河横亘在我们面前,一河被污染的黑水缓缓南流,桥面已塌入水中。
司机听从我们的建议,沿着河东寻路向北驶去,一路上断壁残垣尽收眼底,只有水泥厂的车间孑然矗立。车经过唐山钢厂时,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在人群中忙碌,其中还有一个漂亮姑娘;这是地震后我发现的第一批医护人员,心中不禁肃然起敬。
车行至唐山市第二医院折向西去,这里有一座没断的水泥桥,我们终于过了陡河。
看了城北的一片惨状,李君改了主意,要先去北郊的丰润县看望在那里插队的姐姐,于是便在钓鱼台下了车。
我在车上继续西行,路过西北井我曾住过的土方公司大院时,已不见了昔日的景象,只见邻居张福杰的二妹站在院外。十年后,我作为《中国消费者报》的机动记者,专程赴唐采访震后重建,还去了张福杰家。
车向机场方向驶去,我下了车准备向南,对面走过来两个女中学生,其中一个哭着对另一个说:“我们家人全死了,就剩我一个!”
这是我进入唐山市区听到的第一句话!
一辆卡车从我身后驶来,我伸手扒了上去。车厢内,躺着一位20多岁的女伤员,一身尘土脸色惨白,两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我。
我胸口一沉,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虽然身高仅1.75米,但胸围却有110,更兼满脸倦容 ,整个一条莽汉。我赶紧跳下车,心说:别惊吓了伤员,干脆走吧。
沿西新村向南,只见马路两侧一边躺着一排伤员,里边各有一排死尸,再往里的废墟上,才有没受伤的人在忙活着什么。
人们的着装更是五花八门,穿什么的都有,甚至男人穿裙子,女人围床单的都不稀奇。大震突至,逃命要紧,事后从塌房里能扒出什么就穿什么吧。
行至凤凰山公园的游泳池,一池清水尚在,一个中年男人在用池水擦身。哇,太奢侈了,不要多久,唐山人恐怕都没有水喝了。
我沿工人医院经文化宫奔西山口,这本是唐山市一条幽美的小街,街旁时时可见日式的二层小楼。但此刻,昔日美景荡然无存,惟有断檩残墙在诉说着经历的灾难。
走着走着,我突然惊呆了。一幅我闻所未闻、想未敢想的绝惨画面映入眼帘:一个少妇怀抱婴儿,从一楼的窗口探出身来,被上面落下的砖石双双压死在窗台上……
生者常噩梦,死者恸千魂!
我步履沉重地挪出了这条街,到了西山口百货商场,忽然发现,商场前面跪着二三十人,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他们从商场翻出来的东西,一个脖子上挂衬衫的中年男人哀求着看守他们的持q民兵:“我的两个孩子都没有衣服穿,我不是抢劫的!”回答他的是呵斥。
我快步离开了这里,不想看到人性中恶的一面。
行至路南区,这里灾情更重,连断墙都很少见到,到处是大堆的断砖残瓦。
沿复兴路南行,快到刘屯时,我看到赵国彦站在瓦砾堆上,他和我同在范各庄矿下井,以前又同在遵化插队,他还娶了同村插队漂亮的北京知青。
昔日机敏的赵国彦也看到了我,半天才反应过来:“我们家人全没了!就剩下我一个。”
这是我走出唐山市区记住的最后一句话!
赵国彦大我几岁,我不知怎么安慰他。我打开背着的书包,里边还有十来个饽饽,“你一定没东西吃,咱俩一人一半。”我说。
赵国彦执意不肯,担心我走不到天津,这时候要饭都没地方要。好说歹说,他才勉强留下两个。
出了唐山市区,我沿着公路快步奔向丰南县城。路上,遇到了一男二女三个天津小知青,他们问我回津之路,于是我们结伴而行。 丰南的公路毁损得比唐山厉害,到处是裂缝,大的有一米宽十几米长,汽车已经很难通行。自从我在唐山西北井下车以后,基本就没有汽车驶来。
知青们显然体力不支,坐下休息,拿出他们从村里商店扒出的果酱、果汁让我;太甜了,我招架不了,我带的饽饽他们也难以下咽。
我鼓励他们:再走20里,绕过丰南县城,就会有从别的路上开来的车,我们就可以搭车了。我知道,带着他们,我就更难走到天津了。
丰南的原野,庄稼茂盛,宁静如同昔日;只是路过的村庄,皆被震毁,不时看到一群人在埋尸。
我们艰难前行,小知青们表现出的顽强,超出了她们的性别和年龄。我们终于过了丰南县城,她们累得坐在路边。
身后终于有车开来了,我们起身拦车,但没有一辆车肯停,甚至连速度都不减。我说:“不用躲,别害怕,人多司机不敢压。”但知青们还是不敢。
我只好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找到一处裂缝大、毁损多,到处翻沙的路段,汽车到此必须减速。我说,咱们得在这儿死拦,否则就得走回天津!知青们点头。
等了好久,一辆带蓬卡车开来,我们起身拦住,车不肯停,但已慢如步行。两个女知青用极快频率的天津话求司机让她们上车,我一推她们:“啰嗦什么,赶快上,我一人在前边拦着。”只要她们上去了,我就好办了。
远处有人见来了车,也向这里跑来。押车的战士急红了眼,对我大喊:“我们是奉命拉药的军车,快闪开!”就差拿q对着我了。
我估计知青们已上了车,急忙跑向车后,哪知只是那个男的上去了,两个女的手扒在车厢后档板上身子上不去,男的正往上拽她们。
这时军车已开始加速,我顾不得男女有别,每个人屁股上托了一把,把她们推上车,然后自己也扒了上去。
押车的战士还想让我们下车,我一瞪眼,车后又有两个小伙子扒上了车,车速已相当快了。
车行不久,又被拦住,原来是沿途村民把伤员横放在路中,要求搭车。
车走走停停,不断地被拦,车上挤满了人,又热又臭。
好不容易到了芦台镇,已经是下午了,一条河横在前路,桥早已断了!
听说有工兵要来架桥,我打消了游过去的念头,和大家一起等候。河两边的汽车逐渐排成了长龙。
天真热呀!芦台镇里不时有卡车向外拉尸体,从我们面前驶过,散发出阵阵腐臭。这里震得也很厉害呀!
等到半夜12点左右,简易桥终于可以通行单车了。我们挤上车,期待着过河。
军人指挥交通,先放行对岸的车,大都是军车,满载着救灾物资。我心中一亮,天津可能比唐山受灾轻,震中大概已经在我们身后。
凌晨2时许,我们这边开始过桥,车上的人们长出一口气,终于可以走了!
两个多小时后,汽车到了天津市河北区,大部分的人都下了车。路边的天津市民围上来,一位大姐端着一锅稀饭,招呼我们:“唐山来的,喝点稀饭吧!”
我听了鼻子直酸,这一天多我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军车继续前行,在市委附近,我下了车,走向泰安道11号我的家。这时看清楚了,路两边的房屋毁损比唐山轻多了。
但走进11号院,我的心又揪了起来,门口一幢二层楼一塌到底!
我家在院子最里边,我疾步奔去,见我家房子只是外墙倾斜,屋顶斜搭,尚未趴架,心才放了下来。房子不垮,人就死不了。
在旁边59中学的 *** 场上,我找到了家人,这时天快亮了。弟弟见了我说:“活着哪!”我说:“活着哪。”妈妈端来半锅稀饭,我端起锅来胡乱喝了一气,躺倒在地面的凉席上,“有话明儿再说吧。”便昏然睡去。
我已经近50个小时没睡觉了!
上午9时许,我醒了。好几个人正等着我,他们急切地问我唐山的情况,他们都有亲友在那里。毕竟,我是第一批从唐山灾区来的人。
随后两天,我不断地被周边的人们询问唐山地震的情况,及他们亲友的安危。我反复说:“有一半以上的人活着!”
我把家里稍事安顿,房子也没修,便决定回矿。公路、铁路客货车均已停运,我打听附近的单位,找到一辆去唐山的卡车,便踏上了归程。 唐山越来越近了,远远看去,天格外蓝,以往工厂排出的烟尘罩在唐山上空的黑帽子不见了。只有一架飞机在那里盘旋,走近才知道是在喷药。
车到路南区停下,我拐个弯到同村插队的知青刘仲懿家看看,仲懿和她妹妹正在简易棚收拾东西。她对我说:一家八口就剩下她们姐妹俩,因为都在外县插队,才没死。
我不胜惋惜,陪着她们难过了一阵。至今,我脑海中还有她慈祥母亲和漂亮弟弟的形象。
离开了刘家,我一路扒飞车,回到了矿上,当天就投入了抗震救灾工作。但是,新的灾难正等待着我们——没有房子住,我们的床就放在架高了的自行车棚架下面,夜间蚊帐里总会钻进十来只蚊子。
吃的更不卫生,几乎每平方厘米的食物表面都落有两三只苍蝇,清洁的饮水是想也别想。
几乎人人都在生病,多数是拉肚子。我坚持几天也不行了,高烧加急性痢疾。
我去矿医院的简易棚要“痢特灵”,但看到的景象真让我难过。由于生病的太多,不知是谁怀疑矿工们泡病号,于是决定当场采便化验。只见来就医的矿工们排成队,逐个脱下裤子,跪趴在病床上,由专人拿着玻璃棒捅进肛门采便。
我气愤得扭头便走。我宁可不拿药,不领病假工资,也不受这人格和身体的双重欺辱!
接下来的日子,我躺在床上,曾经身强力壮的我需要扶着东西才能站起来。我索性绝食绝水,肚子里的脏东西拉光了,病自然会好,我寄希望于自己的抵抗力。
北京知青小王,给我拿来了一瓶水。他说:你放心喝,这是我在塌陷坑边筑沙坝过滤的水,用饭盒烧开了。
9年后,我考上了记者,去过不少地方,喝过各种各样的饮料,但都没有这瓶水情深义重!只可惜,后来不知他去向何处?时间过去了30年,连他的名字也忘却了。
绝食三天后,我觉得自己病好了,不用扶着东西能站起来慢慢走了。我觉得自己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新人!
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这“后福”是人变坚强了,不会被一般的困难摧垮了。
情况一天天好起来,尽管我在后来的救灾工作中,因疲劳摔致左脚骨折,但毕竟最艰难的时日已经过去。
矿工们用断砖在自行车棚周围砌起了墙,并间隔成十几平米的小间。张新伟把一瘸一拐的我安顿进他们的小棚屋,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生火过冬的栖身之所了……
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震级7.8级,24万人死于瓦砾,16万人重伤,7000多个家庭断门绝烟!
我和几个京津知青,有幸与唐山人民共赴大难:奋挣扎之力,遣伤病之躯,关心互助,风雨同舟;慷慨悲歌壮曲,同至涅(般/木)重生。
不是。在1946年底,世界上一项新的发明诞生了:这就是晶体管。从一开始人们就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精灵会永远地改变收音机。这确实发生了,但并不是在一夜之间。第一个商品化的收音机于1954年面市 ( Regency TR1, 现被收藏者严重破坏)。 菲力普在采用新技术时总是慢半拍,事实上,菲力普对开发老产品做的不错。但是在1957年,他们终于等不住了,推出了第一个便携式收音机,这就是L3X71T。六七十年代,收音机就是一个家庭的重要财产。许多中学生、大学生要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收音机,只能自己组装。他们就像今天的学生们组装电脑一样,买回一堆二级管、三极管、电容、电阻一类的东西,然后对着电路图装配。就连收音机的外壳也是用三合板自己做成的。
电子工业是20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党和国家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陆续建立了一批生产电子产品的骨干工厂和科学研究单位。 1958年,上海宏音无线电器材厂,天和电化厂等9个工厂及上海无线电子技术研究所联合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此后,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一些无线电工厂先后生产出“春蕾”、“飞乐”、“红灯”等半导体收音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相“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
半导体收音机是谁发明的
在1844年,电报机被发明出来,可以在远地互相通讯,但是还是必须依赖「导线」来连接。而收音机讯号的收、发,却是「无线电通讯」;整个无线电通讯发明的历史,是多位科学家先后研究发明的结果。
1888年 德国科学家赫兹 (Heinrich Hertz),发现了无线电波的存在。
1895年 俄罗斯物理学家波波夫 (Alexander Stepanovitch Popov),宣称在相距600码的两地,成功地收发无线电讯号。
同年稍后,一个富裕的意大利地主的儿子年仅21岁的马可尼 ( Guglielmo Marconi)在他父亲的庄园土地内,以无线电波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发射。
1897年 波波夫以他制做的无线通讯设备,在海军巡洋舰上与陆地上的站台进行通讯成功。
1901年 马可尼发射无线电波横越大西洋。
1906年 加拿大发明家费森登 (Reginald Fessenden)首度发射出「声音」,无线电广播就此开始。
同年,美国人德.福雷斯特 (Lee de Forest)发明真空电子管,是真空管收音机的始祖。之后到现在 又有改良的半导体收音机(原子粒收音机)、电晶体收音机出现。
为什么叫半导体收音机
因为半导体晶体管的第一个商业化产品就是半导体收音机。
收音机在刚出现的时候是用的真空管,后来半导体晶体管出现了,而半导体所制作的第一个商品就是收音机,所以半导体也就成了半导体收音机的代称了。
同时也是为了区分真空管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
半导体收音机的原理
收音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人类自从发现能利用电波传递信息以来,就不断研究出不同的方法来增加通信的可靠性、通信的距离、设备的微形化、省电化、轻巧化等。接收信息所用的接收机,俗称为收音机。目前的无线电接收机不单只能收音,且还有可以接收影像的电视机、数字信息的电报机等。 随着广播技术的发展,收音机也在不断更新换代。自1920年开发了无线电广播的半个多世纪中,收音机经历了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集成电路收音机的三代变化,功能日趋增多,质量日益提 高。20世纪80年代始,收音机又朝着电路集成化、显示数字化、声音立体化、功能电脑化、结构小型化等方向发展。
广播电台播出节目是首先把声音通过话筒转换成音频电信号,经放大后被高频信号(载波)调制,这时高频载波信号的某一参量随着音频信号作相应的变化,使我们要传送的音频信号包含在高频载波信号之内,高频信号再经放大,然后高频电流流过天线时,形成无线电波向外发射,无线电波传播速度为3×108m/s,这种无线电波被收音机天线接收,然后经过放大、解调,还原为音频电信号,送入喇叭音圈中,引起纸盆相应的振动,就可以还原声音,即是声电转换传送——电声转换的过程。
半导体收音机发展大事件盘点
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在上海创办中国无线电公司,播送广播节目,同时出售收音机,以美国出品最多,其种类一是矿石收音机,二是电子管收音机。
1953年,中国研制出第一台全国产化收音机(“红星牌”电子管收音机),并投放市场。
1956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只锗合金晶体管。
1958年,我国第一部国产半导体收音机研制成功。
1965年,半导体收音机的产量超过了电子管收音机的产量。
1980年左右是收音机市场发展的高峰时期。
1982年,出现了集成电路收音机和硅锗管混合线路和音频输出OTL电路的收音机。
1985年至1989年,随着电视机和录音机的发展,晶体管收音机销量逐年下降,电子管收音机也趋于淘汰。收音机款式从大台式转向袖珍式。 [编辑本段]收音机历史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奥斯邦氏与华人曾君创办中国无线电公司,通过自建的无线电台首次在上海播送广播节目,同时出售收音机。全市有500多台收音机接收该电台广播节目,这是上海地区出现的最早一批收音机。之后,随着广播电台不断的建立,收音机在上海地区逐渐兴起,均为舶来品,以美国出品最多,其种类一是矿石收音机,二是电子管收音机,市民多喜用矿石收音机。
1924年8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公布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定,允许市民装用收音机。市民中装置收音机者渐起,其方法以再生式线路联接为多。同年8月,上海俭德储蓄会颜景焴采用超外差式线路联接法装置收音机成功。翌年10月,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在松江图书馆内,试验组装的矿石收音机与电子管收音机获得成功,不仅收到上海电台的无线电电波,同时也收到日本电台所播的音乐节目。
1933年10月,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了1001号矿石收音机,外形小巧美观,价格低廉,收音良好,受到市民欢迎。1935年10月,该公司生产出第一台1651型超外差式五灯收音机。该机除电子管和碳质电阻外,所用的高周与中周变压器及电源变压器和线圈均自行设计制造。此后,一批无线电制造厂相继生产收音机。其中以中雍无线电机厂规模较大,仅次于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生产出标准三回路一灯收音机与直流三灯收音机等产品。此外,尚有华昌无线电机厂、亚尔电工社等,都先后生产过一灯到五灯收音机。虽然生产手段较落后,产品数量不多,但这些产品在国内无线电制造业中占有一定地位。
1936年,随着广播电台事业的发展,收音机在全市逐步普及,总数约在10万台以上,但几乎都是国外制品,使得国内民族无线电制造业发展缓慢。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无线电制造业进一步受到打击。1942年,侵沪日军禁止市民使用七灯以上的收音机,并强迫市民拆除收音机的短波线圈,各无线电制造厂在日伪统治下,生产陷于停滞状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民族无线电制造业重新得到恢复,同时又发展了一批新的无线电厂商。1947年年底,上海电器工商业共有590家,其中无线电工商业为235家。同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上海建立研究所,制成资源牌台式和落地式八灯高档收音机。但由于官僚资本企业从国外进口大批成套无线电零件,低价销售组装收音机,给民族无线电制造业带来新的打击。至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电讯工业约有30%以上工厂处于停工与半停工状态,从事收音机及其零件制造的仅剩7家工厂和工场,从业人员共113人。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