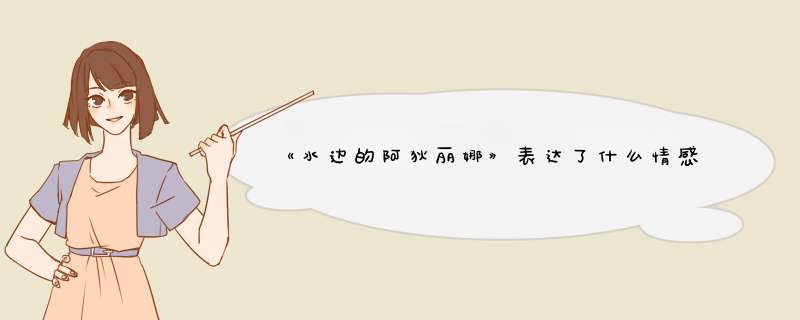
《水边的阿狄丽娜》就是对理查德·克莱德曼心中最完美的那个人的勾画。因为你无从表述你心中最完美的爱人是怎么样的,只能用心感觉,在心里勾勒。在婉转悠扬的琴曲声中,琴键上跃动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和他的完美情人,而听众内心浮现的,是个人对完美的定义。
实际上表现了一种对人物阿迪利娜的赞美诗。作者用巧妙的音乐语言,加上理查得·克莱德曼的精湛演义,表达了一种很神秘的意境。
在音符讲述的故事里,阿迪利娜在水边撩起的不是水波,而似乎是轻纱。理查得手指微触及琴键所发出的音符,充满罗曼谛克式的醉人芳香。
水边的阿狄丽娜
水边的阿狄丽娜,法文名:Ballade pour Adeline原名:致爱德琳的诗,是由保罗·塞内维尔所作,理查德·克莱德曼(Richard Clayderman)演奏的乐曲。1990年,理查德·克莱德曼以演奏作曲家兼经纪人Olivier Toussaint改编版的《给爱德琳的诗》获得金奖。
此曲是通俗钢琴曲,对于频繁出现的六度的不同强弱的深入浅出,你要做出轻重的对比,在C段中稍稍有一点难度,应确保把左右手衔接无缝隙,多练。踏板问题,要注重用耳朵去听,录音会给你帮助的。
其次,就是表达力,通常我们从音乐的标题入手。譬如,这开始的几处重复,表现了水的波纹,那么你要d得清荡。同时也要注重和声的变化色彩。
对莎士比亚《理查德三世》的心理分析(一) 莎士比亚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戏剧巨匠,马克思把他和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看作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的两个最伟大的天才戏剧家”。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里,无数学者与评论家都热中于对他及他的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有关莎翁及其作品的书籍层出不穷。不过仔细探讨过去的莎学研究,我们发现对于莎蓊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经典作品方面;在历史剧的研究中,学者们又多集中于《亨利六世》和《亨利四世》。与其他的历史剧相比,学者们对于《理查德三世》的研究是最少的,而且对它的研究也主要局限于批判理查得三世的残忍和不择手段。其实,《理查德三世》这部历史剧堪称为人物心理历程的巨作,正如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如果说理查是心理学家们所注意的第一人,在他之后则还有理查二世、奥瑟罗、伊阿古、麦可白、麦可白夫人、李尔王、里昂提斯等等—他们对现代心理分析学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它是一部莎士比亚最早把心理分析运用到艺术表现中的作品,莎士比亚在剧中具体生动地展示了理查德三世之所以成为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心理原因和心理过程。理查德三世是一个从身心到身体都丑陋无比的暴君,他为了登上不属于自己的帝位,满足自己的野心,总是不择手段,在任何的罪恶面前,都毫不踌躇。这样,在他通往王位的路上,布满了他的兄弟、侄儿、大臣的尸体,洒满了无辜者的鲜血。那么促使理查得一步步走向血腥暴力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为什么和他同父同母的克莱伦斯公爵就那样的与他截然不同?要揭示出理查得三世的心路历程,我们还须借助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释梦理论和本能理论等。(二) 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创立了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石,它对临床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可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它的核心理论包括:精神层次理论、人格结构理论、本能理论、性欲理论、释梦理论和心理防御机制理论等。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人格结构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的。“本我”即原我,是潜在人的无意识深处的部分,它是最原始、与生俱来的、非理性的种种本能、欲望和生命力的冲动。本我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不理会社会道德与外在的行为规范,它惟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自我”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它是“本我”和外部世界、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居中者,它调节着“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把所有的能量都消耗在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的控制、压抑和排除上,所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即“道德化了的自我”,是人格结构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包括良心和自我理想两部分,其机能主要在于监督、批判及管束“自我”的行为,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弗洛伊德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上述三个部分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当三者发生冲突时,平衡遭到破坏,即导致变态的心理。[1] 让我们来看看理查德的身世。理查德是约克公爵的第四个儿子,在爱德华四世时期被封为葛罗斯特公爵。从“本我”的层次来看,理查德三世深知作为王室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取得皇帝的职位,成为他的对手。于是,他先当着玛格莱特的面,杀死她年幼的儿子。不久,又闯入塔狱,把玛格莱特的丈夫亨利六世刺死。杀死亨利王父子是实现他野心勃勃的远大目标的第一步。然后他恶毒的眼光开始盯住自己家中可能与他竞争王位的继承者。如果按世袭继承的规矩来排,王位距离他是很遥远的。在他们兄弟几人中,他是老四,老大是国王爱德华四世。而且他前面的兄弟们都有后嗣,所以他非杀开一条血路才能摘取金灿灿的王冠。当他开始清除家族内部王位继承者们的“第二套行动计划”时,他首先准备干掉的是他的三哥克莱伦斯公爵。他自言自语道:“亨利王和他的儿子爱德华王子都已完蛋,克莱伦斯,现在就轮到你头上了。我要把这伙人一个个都解决掉。”理查德是个有意志、有决心的人,而且说做就做,非成功不可。他给自己提出最艰巨的任务,而且以自己的成功为乐。这是理查得三世“本我”的体现。从“自我”的层次上看,要采用“现实原则”,他还不能明目张胆地杀害他的兄弟克莱伦斯,所以采用了借刀杀人的方法。他支使人通过占卦来制造谣言,使患病的爱德华四世相信克莱伦斯是一个阴谋篡位者,把他关进了塔狱。理查得假惺惺地同情克莱伦斯,并使他相信这都是王后等人使的坏。可怜的克莱伦斯被害前还盼着理查得来救他出去,他哪里能想到两个恶魔般的刽子手就是理查得派来的呢?克莱伦斯给处掉了,爱德华四世也病死了,耀眼的王冠已经胜利在望了。这个时候理查德三世的“自我”一直在为“本我”服务,也就是说一切的阴谋诡计要为王位服务。理查德三世的终极快乐是黄袍加身,所以他使出浑身解数,来收拾最后几个障碍。他的大哥爱德华四世有两个天使般的小王子,在他们的父王驾崩后理应来继承王位。理查得也虚情假意地和群臣商议王子继位的事,却把两位王子诱骗到伦敦塔中,然后支使凶手们活活勒死了他们。对两个天真的孩子下此毒手,真是惨绝人寰。连凶手们“听了那番临死前的悲诉,也竟象顽石点头,象孩子一般流下热泪。”与此同时,理查德又把克莱伦斯的傻儿子关了起来,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穷人。王后伊丽莎白的兄弟和前夫之子也被处死了。至此,整个王室除了伊丽莎白王后和她的女儿小伊丽莎白外,全部被理查德三世斩尽杀绝。王位已经是唾手可得。可是,为了名正言顺地等上王位,理查德三世的“自我”再次为他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他一边对公众舆论进行欺骗,一边对大臣中持反对意见的人进行镇压。海斯丁原是支持理查德对王后的亲属进行报复的人,但后来因积极主张为爱德华的两位王子早行加冕礼,就被理查德找个借口杀掉了。他最可靠的亲信勃金汗,最后也被他杀掉了。就这样,理查德三世等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宝座,同时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本我”、“自我”和“超我”必须处于平衡的地位,如果一方无限膨胀或无限缩小,结局一定是人格不完整。在理查德三世的身上,足智多谋、能言善变、坚定果断和随机应变一直是他“自我”的体现。他不愧为一个恶天才,能如此轻松地驾驭和控制那些善良而单纯的人们。他笑里藏刀,口蜜腹剑,在吃人之前总要扮成一个虔诚的圣徒,用花言巧语骗取对方的信任,然后待时机成熟,才现出自己狰狞的本相,将牺牲者一口吞下。他的“自我”是一直为他的“本我”服务的。成为国王、杀掉他的一切障碍,这是他的终极快乐,是满足他的野心、实现他的梦想的途径。如果从“超我”的层次上看待理查德三世的话,“超我”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它的机能主要在于监督、批判及管束“自我”的行为,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冲动。可是我们看到理查德三世的“超我”在“本我”面前是多么的无能为力,他对社会道德准则的无所顾忌和无法抑制的野心,使他意识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难以平衡,他的心理和行为与社会道德准则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他的善性被压抑,恶性日益彰显。由于他的心理产生障碍,性格产生缺陷,精神产生分裂,他一定会走到社会的对立面上。(三) 梦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严格的因果关系,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梦也不例外。梦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欲望的满足。在睡眠时,“超我”的检察开始松懈,潜意识中的欲望绕过抵抗,并以伪装的形式,悄然溜入意识而形成梦,可见梦其实是对清醒时被压抑的潜意识中的欲望的一种委婉表达,是通向潜意识的秘密通道。通过对梦的分析可以实现人的内部心理的剖析,探究其潜意识中的欲望和冲突。[2]弗洛伊德还认为,成人的梦大多是象征的、经过化装的,象征的用意在于逃避检查。我们梦中的所见所闻都是梦的化装,而不是梦的真面目。梦的化装称为“梦的显象”,而潜藏在梦中的意向和情景后面的真实欲望则是“梦的隐义”。把梦的隐义化装成梦的显象是“梦的工作”,而从梦的显象中寻找出梦的隐义则是“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认为,梦形成的主要动力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本我”内的各种本能冲动,第二种实际是介于“本我”和“自我”之间的“检查机制”以及“自我”和“超我”本身。在无意识中被压抑的这些材料,通过梦反映出来,只有在睡梦中,检查机制才放松它的警觉,才以各种形式的梦表现出来。在《理查德三世》中,理查得和里士满决战的前夕,理查得看到的“幽灵”以及他们对他的控诉,都是理查德内心“无意识”的流露。在梦中,他的“本我”帮助我们深入地分析他的思想状态,破译他的情感心理密码。 在梦境中,理查德三世的亲人和大臣,像亨利六世之子爱德华亲王、亨利六世、克莱伦斯、两个小王子、安夫人和勃金汗等一一登场,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在谴责理查德三世的罪恶,同时又都在为里士满摇旗呐喊。清醒的时候,他一直为自己的胜利得意忘形,为他自己沾满鲜血的王位而洋洋得意;但是在梦中,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就袒露出来了。虽然在意识中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悔意,但是当处于无意识的梦中时,他人性中的那一点善就流露出来了,表现了“本我”的善良。梦醒之后,理查德心里想到:“……呵,良心是个懦夫,你惊扰得我好苦!……这儿有凶手在吗?没有。有,我就是;那就逃命吧。……呀!我其实恨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干下了可恨的罪行。我是个罪犯。不对,我在乱说了;我不是个罪犯。……我这棵良心伸出了千万条舌头,每条舌头提出了不同的申诉,每一申诉都指控我是个罪犯。犯的是伪誓罪,罪大恶极;谋杀罪,残酷的谋杀罪,罪无可恕;种种罪行,大大小小,拥上公堂,齐声喊道:‘有罪!有罪!’我只有绝望了。天下无人爱怜我了;我即便死去,也没有一个人会来同情我;当然,我自己都找不出一点值得我自己怜惜的东西,何况旁人呢?我似乎看到我所杀死的人们都来我帐中显灵;一个个威吓着明天要在我理查头上报仇。”[3]可见在理查得三世的心中还有善心的,也有悔意,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悖天理,“超我”体现出来了,在人之将死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超我”才压抑住了“本我”中的恶,“本我”中的善才显露出来。(四)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有两类:一类是生的本能,另一类是死亡本能或攻击本能。生的本能包括性欲本能与个体生存本能,其目的是保持种族的繁衍与个体的生存。弗洛伊德在后期研究中提出了死亡本能即桑纳托斯,它是促使人类返回生命前非生命状态的力量。死亡是生命的最后稳定状态,生命只有在这时才不再需要为满足生理欲望而斗争。死亡本能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是其能量向外投放,表现为破坏性、攻击性、挑衅性、侵略性,或争吵、欧斗、战争等形式。另一种是其能量向内投放,表现为自责自罪,自我惩罚,自我毁灭,自残自杀等形式。[4] 《理查德三世》中的理查得天生一副畸形陋相。出生时就“两腿先下地,满嘴长牙”,显出一付凶相。长大后,他的一只胳膊萎缩得象根枯枝,脊背高高隆起,两腿一长一短,没有一部分是匀称的。在他狰狞的外貌下是他邪恶的内心,外形的丑陋和灵魂的丑恶是一致的。由于他奇丑的外貌,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似乎都与他无缘。如果他是平民,可能对自己的处境泰然处之。可他偏偏又是个地位特殊的人,是个王族的显贵,又有着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勇气。这就使他感情上产生了极大的痛苦,转而对一切人产生憎恨和报复的感情,有了毁灭一切的变态心理。特别是当他听说有人传说爱德华的继承人之中有个G字起头的要弑君篡位,他和乔治克莱伦斯都是以G起头,所以他大开杀戒。这是他杀人的借口,但也是他死亡本能的一种表现。根据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有时自我为了求得生存,尤其是在对待来自死亡的危险时,人也会力图通过改变本能选择了转移危险。也就是说,把死亡本能从自身引开,转移为对外界的攻击,破坏,竞争等欲望,以此来转移自身的危险。”[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他把他的屠刀开向他的亲人时,他潜意识中的死亡本能发挥了作用,他的生存本能迫使他的死亡本能转移为杀害克莱伦斯,再加上他原来的野心,才产生了以后的种种恶行。如果理查得三世不是这样一副丑陋的外形,从小可以得到父母的怜爱和亲人的友情,同时他本身智勇双全,如果能有一段时期,有那么一个人能够注意到他的潜力并加以引导,使他有机会表现和发展他的才能,也许他经常感到的自卑、排挤以及对整个家庭乃至世界的妒恨会因对自我的认可而逐渐减弱,也许他内心的狂暴因子也会慢慢消失。 (五) 从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释梦理论和本能理论可以看出理查德三世是一个人格不完整的人,他的生理缺陷和家庭的排挤造成他心理的畸形发展。在与别人的攀比中,他发生了嫉妒,嫉妒别人的外貌,别人的快乐,别人的爱情和幸福。这些似乎都已注定是他享受不到的。他只有靠不正当的手段才能达到他的目的,但也因为如此他才丧尽天良,恶贯满盈,走到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上去,所以他最后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理查德的内心表现,伴随着他的每一个行动,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君王心理史。为了表现理查德的意识和潜意识中流动的东西,表现他深层结构中的思想和感情,莎翁主要采用了独白的形式。这在他的别的历史剧中是不多见的。莎士比亚是最早把心理分析运用到艺术表现中的作家。这种手法使艺术形象更丰满,更生动,更完美,更有血有肉,使人们不仅看到人物形象的形体,也看到了灵魂。正是莎士比亚的独特心理表现手法,才使得《理查德三世》能作为一部独幕式的心理分析剧而为后人所赞扬。他使人们对一个野心家、阴谋家的全部内心世界能有清楚的一瞥,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理查德三世所》蕴含的典型意义。钢琴曲《水边的阿狄丽娜》表达的是一种对爱的期盼、渴望。
《水边的阿狄丽娜》创作背景来源于希腊神话,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孤独的塞浦路斯国王,名叫皮格马利翁(Pygmalion)。他雕塑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每天对着她痴痴地看,最终不可避免地爱上了少女的雕像。
他向众神祈祷,期盼着爱情的奇迹。他的真诚和执着感动了爱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赐给了雕塑以生命。从此,幸运的国王就和美丽的少女生活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水边的阿狄丽娜》是由保罗·塞内维尔所作,理查德·克莱德曼(Richard Clayderman)演奏的乐曲。1990年,理查德·克莱德曼以演奏作曲家兼经纪人Olivier Toussaint改编版的《给爱德琳的诗》获得唯一的金钢琴奖。
扩展资料
《水边的阿狄丽娜》各种版本
1、Richard Clayderman演奏的《水边的阿狄丽娜(Ballade pour Adeline)》,该歌曲收录在专辑《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曲全集-水边的阿狄丽娜》中,2004-01-01发行,该张专辑包含了10首歌曲。
2、HJGEEK演奏的《水边的阿狄丽娜 (钢琴教学版)》,该歌曲收录在专辑《HJGEEK速成钢琴》中,2017-07-21发行,该张专辑包含了10首歌曲。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