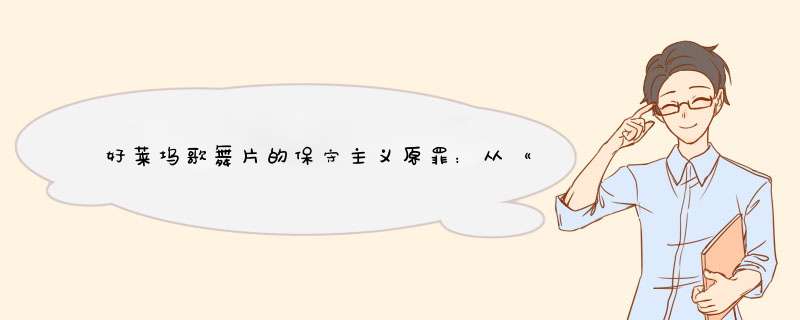
“被遗忘的人”与好莱坞歌舞片的黄金时代
1932年,美国大萧条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9),民生凋敝,25%美国人处于失业状态。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1933年起实施“新政”(New Deal),救济工人,保障工会,复苏经济,管控金融体系。罗斯福在广播讲话中呼吁将财富更公平分配给“被遗忘的人”(forgotten men)。2016年,纽约房地产商特朗普当选总统。人们说,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严重伤害利益的“锈带地区”工人,是促成特朗普当选的重要力量。尽管罗斯福代表的,是偏左的“自由派”(liberal),特朗普代表的,是带有白人男性中心色彩的右翼民族和民粹主义,甚至财阀政治,这八十年间的历史轮回中,同样被“遗忘”的白人男性工人以不同方式反d,也会迎来不同后果。
“被遗忘的人”这一表征,也在好莱坞歌舞片《1933年淘金女郎》(Gold Diggers of 1933, 1933)中得到呼应。女主角与女伴沧桑唱起“记得我被遗忘的男人”(Remember My Forgotten Man),画面出现无数曾参与“一战”、然而在“大萧条”中被抛弃和遗忘的、排队领救济的衣衫褴褛的美国白人男性。此时,好莱坞也迎来“歌舞片”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电影史家认为,生计艰辛时,人们更需要逃避型娱乐,躲进黑暗的影院,在歌舞奇观和感官刺激中暂时忘记苦难;何况,自1927年有声电影始,歌舞片这种类型可有效利用声音这一电影新技术。这也是美国西海岸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东海岸纽约的百老汇歌舞剧及流行唱片业物质与人才资源的密切合作。出产有声歌舞片《42街》(42nd Street, 1933)、《1933年淘金女郎》、《华清春暖》(Footlight Parade, 1933)的华纳公司因而在三十年代声名鹊起。如上所述《1933年淘金女郎》中场景,在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歌舞奇观中,出人意料地表现都市混乱与贫困,可见当时歌舞片也并未完全与电影院外的社会现实绝缘,观众看到此处,也会从幻梦中凛然一惊吧。
歌舞片在1970年代后作为一种“老派过时”的类型逐渐衰落,偶尔有几部在漫长电影史里煊然点缀,如《红磨坊》(2001)和《芝加哥》(2002)。在美国大选后混乱迷惘的2016年末,又出现一部令美国观众、影评人、奥斯卡评委一致好评的歌舞片,达米安·查泽雷(Damien Chazelle)编剧和导演的《爱乐之城》(La La Land, 2016)。这是一部“东西合流”、新旧混杂的电影,在不同层面微妙地切中时代脉搏、恰合人们心态。说“东西合流”,因导演为出身美国东岸的精英(读精英社区的普林斯顿高中、在哈佛大学学电影、在纽约拍过广告片),2010年搬去西岸洛杉矶,在好莱坞的名利场中终于因《爆裂鼓手》(Whiplash, 2014)和《爱乐之城》崭露头角,与西海岸资本合流。说“新旧混杂”,因《爱乐之城》从头至尾都在向以歌舞片为代表的好莱坞技术美学与娱乐遗产致敬:宽银幕、怀旧彩色、舍数字而用胶片拍摄,以及层出不迭的引用好莱坞老电影及法国导演雅克·德米歌舞片《瑟堡的雨伞》(1964)、《柳媚花娇》(1967)桥段的痕迹。不过归根结底,与《1933年淘金女郎》不同,《爱乐之城》与当下社会现实并无直接关联,其关乎的,只是个体的野心、挫败、感伤与成功。这,也正是它商业与评论皆成功的秘诀。而据说好莱坞各公司正在投拍二十多部歌舞片,这不能说不是该类型的又一个小高潮,也似乎是对三十年代社会政治与歌舞片类型关系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回应。
歌舞片的意识形态:“漂白”的乌托邦与腐朽的性别观
《爱乐之城》剧照
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认为歌舞片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是关于“乌托邦的感觉而不是它如何被建构”。这种乌托邦的幻觉,与其实质无关,后者也非歌舞片兴趣所在。《爱乐之城》的开篇镜头,便营造了这样一种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乌托邦:令人头疼的洛杉矶交通阻塞催生了一场浪漫绚丽、活力四射的盛大歌舞狂欢。在这个长镜头里,各种肤色、族裔、性别的人都在“政治正确”、“文化多元”展览场里尽情阐释什么是和谐欢乐祥和团结。然后,回到片中现实。镜头切向男、女主角,当然都是白人,都是金/红发。男女主角由冤家对头到异性爱侣,这是传统歌舞片叙事的约定俗成。接下来他们漫步于幽静山路、出入游泳池豪宅的鸡尾酒会、有现场音乐伴奏的饭馆、爵士酒吧、古老小剧场、怀旧电影院……在这些布尔乔亚情调的漫游中,历史与现实中的贫困隔离、人数众多以至于无法让人视而不见的少数族裔被影片当作“噪音”消除和“净化”,于是,洛杉矶这个镌刻着种族矛盾骚乱伤痛的喧嚣城市变得如此整洁空旷,浪漫非常,只属于我们的男女主角和他们同样优雅的同类。在此,怀旧是一种特权。在男女主角怀恋的好莱坞黄金时代,也是很多公共空间“有色人种不得入内”、或需另辟入口和洗手间的时代。因为种族、肤色和消费能力,他们被区隔和排斥。这种怀旧,对某些族裔来说,是种灼人的伤痛。
这点上,《爱乐之城》忠实沿袭好莱坞歌舞片传统的“文化盲点”(cultural blind spot)。歌舞片种族、性别偏见、粉饰太平的“原罪”大约不逊于西部片,如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言,歌舞片中,族裔、阶层、地域、性别的差异被抹去,焦点永远毫无争议是白人明星(漫长的歌舞片历史中,以非裔人物为主角的电影屈指可数,有也主要面向非裔观众)。与非裔音乐家在美国流行音乐和娱乐工业中的巨大贡献和影响相比(如拉格泰姆音乐(ragtime)、爵士、布鲁斯、踢踏舞等),他们在歌舞片中的银幕呈现少得可怜,偶有也是昙花一现。美国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 1927)中,犹太歌手演员Al Jolson将脸涂黑扮黑人演出。这种白人演员以烧焦的软木涂黑脸部、以夸张方式演绎黑人音乐的行为,被称为“blackface”,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歌舞片中较为常见,源于十九世纪的minstrel show,且这是种族主义偏见的美国青出于蓝的独创,为欧洲所无(好莱坞电影也不乏白人演员将眼睛眯斜、肩膀耸起扮亚洲人,称为“yellowface”,从格里菲斯《残花泪》到赛珍珠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大地》)。这种“美式娱乐”作为文化象征暗示同质的国家身份,不问根源,以有魅力的白人身体呈现。
“漂白少数族裔音乐,边缘化非裔乐手”是好莱坞歌舞片的惯用手段。如果说二十到四十年代好莱坞歌舞片种族歧视的核心为“黑人原始主义”(primitivism):爵士乐的盛行是因为白人在那里找到他们自己被现代文明规训而消失的“原始活力”,那么《爱乐之城》中编导者嗤之以鼻、居高临下批判的,是“黑人功利/商业主义”:透过导演/男主角塞巴斯蒂安/女主角米亚的视角,我们看到著名黑人乐手John Legend扮演的Keith搞的黑人狂歌劲舞,向大众和商业妥协,是追名逐利、不懂得爵士乐精神的庸众;而影片结尾终于得偿所愿开了自己的爵士酒吧、要将“纯粹的”爵士乐传承下去的塞巴斯蒂安,在昔日女友米亚的注视下,坐在钢琴(欧洲古典音乐及社会阶层象征意味)前,来一段“拯救黑人爵士乐”的布尔乔亚的轻盈感伤。象征爵士乐“纯粹性”、历史感与民间活力的萨克斯、贝斯、鼓,及先前春风得意的黑人乐手Keith,都悄悄隐退一边,将中央舞台让给白人男性权威塞巴斯蒂安,及他格调并不怎样高明的、中产阶级白人趣味的“纯粹爵士乐”。
这样明显的种族和阶层置换,也对《爱乐之城》作为当代歌舞片本身形成反讽与映照。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矛盾:编导者一面故作清高嘲讽黑人流行音乐亵渎“纯粹爵士乐”,一面制作了部媚俗的歌舞片,即,以“反庸俗大众文化”的姿态,制作包装精巧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另一方面讲,导演“提升”歌舞片这一受轻视的“过时”的类型并将其变得“时髦”的野心,如塞巴斯蒂安要令传统“纯粹”爵士乐重生并符合中产阶级趣味地“优雅化”的苦心并无二致。于是,爵士乐与歌舞片,在导演查泽雷手中都由“低端”升级为“中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流行文化,也重新伟大了。《爱乐之城》看似对欧美歌舞片“引经据典”,却是对“桥段”去历史化的浮夸使用,这种对装饰性和炫耀性的迷恋来包装怀旧的“高尚趣味”,看似“去政治化”,却有意无意重新确认陈词滥调的等级秩序。在这个秩序里,欧洲-法国-巴黎仍是文化与理想的灵感火焰,“亚非拉”和少数族裔(包括配角谈及中国及电话对话里一句“谢谢”)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点缀,以彰显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性理解世界主义与文化多元重要性的眼界与胸襟。
《爱乐之城》作为歌舞片,其类型在电影史上是被“性别化”的:与西部片显而易见的“男性”特质相比,电影学者认为歌舞片是“女性化”的,且四、五十年代歌舞片观众也以女性为多。然而并非“女性化”的电影便是从女性视角叙述或关注女性主体性。“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式歌舞奇观多以衣着暴露的女性身体为卖点,而庸俗但有心机的金发女郎“钓金龟婿”的故事也被歌舞片津津乐道。女性的被物化及政治保守时代“人种优越”论还体现在五十年代彩色电影中对性感金发女郎的迷恋,如霍华德·霍克斯导演、玛丽莲·梦露主演的歌舞片《绅士更爱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1953)片名所示。受过精英教育的《爱乐之城》编导者查泽雷当然不会在当代复制这套保守腐朽的性别价值观(尽管对金发女郎的迷恋也显而易见:金/红发蓝眼白肤是他对理想女性的审美构建):他片中的男、女主角平等、自立、彼此鼓舞,当然,塞巴斯蒂安有责任启蒙将“纯粹爵士乐”理解为肯尼基式“电梯音乐”的无知少女米亚,最终也是他的坚持和鼓励成全了她的演员梦。他为了她的期待而加入商业乐队放弃梦想,终于还是开了自己的爵士酒吧,在嫁做人妇的昔日女友面前,以怀旧感伤音乐作为献给她的心曲和纪念……正如前文提到《爱乐之城》延续歌舞片的种族阶层置换但将其从“保守过时”重新定义为“年轻时髦”,它也将这“女性化”的类型重塑为展示优雅精巧中产阶级白人“男性气质”。尽管片中男女角色戏份旗鼓相当,但核心价值观是男性中心,这是高妙的障眼法,就像开头出现各种族裔,其实绝对主角还是白人。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个体经验如何成为最大公约数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接受与认同,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的高明之处。
个人主义成功学在大众文化中的运作
《爱乐之城》剧照
学者安德烈亚斯·海森(Andreas Huyssen)认为,高级文化,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都是男性行为的特权领域。历史与现状也的确如此。《爱乐之城》将爵士乐和歌舞片重塑为“高级文化”同时,也在重塑男性权威:新的等级次序中,上中产白人男性在金字塔顶端。如果说《爆裂鼓手》的导演自况意味里还有“怀才不遇”的愤懑,《爱乐之城》则多了几许“回顾来时路”游刃有余的自信与自嘲。在这两部电影里,有评论者和观众看到查泽雷对爵士乐的迷恋,细思却不大看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及他是否理解音乐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两片中男主角、导演的“另我”(alter ego)谈论起著名黑人爵士乐手Charlie Parker时,不是他的音乐和演奏精神如何影响人们对音乐的理解,而是“他改变了历史,让人们记住了”。目标明确:“成功”就是一切,让世人尊崇,历史铭记。披着理想的外衣。精英教育和社会阶层造成的智识上的优越感,会使人在“崇拜一切,而什么都不重视”(worship everything and value nothing)的好莱坞忍不住要卖弄、获取赞赏、接受臣服、自我加冕。当然,在好莱坞这个等级森严的名利场与无情的工业体系中,在通往被承认和尊崇的阶梯上,总有挫折与屈辱。正如塞巴斯蒂安和米亚,以及演员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与艾玛·斯通(Emma Stone)所经历过的。然后,他们适应了这套游戏规则,是为成功。
这种寻求理想过程中四处碰壁对个体造成的精神伤害,不仅好莱坞业内人士看了感同身受,普通观众、影评人、奥斯卡评委看了也会心有戚戚。观众的认同感,是影片成功的关键。《爱乐之城》聪明地超越传统好莱坞歌舞片的两个局限:一为因太过注重歌舞奇观,没有足够空间铺陈人物情感深度,二为歌舞形式感与电影写实主义的矛盾,因而缺乏情绪维度的感染力。《爱》将歌舞片场景与情境日常化,讲述“普通年轻追梦者”故事,以人物情绪为叙事中心,歌舞场景皆与叙事推进及情绪变化相关,年轻观众易产生共鸣——四十年代时,美国青少年喜爱歌舞片,如今主流商业电影和小清新独立电影的消费主体亦多为年轻人,与查泽雷这个年轻创作团队的情绪表达方式和观念不谋而合。塞巴斯蒂安这个号称穷困潦倒、视金钱为粪土的爵士追梦者却过着舒适的都市年轻雅痞生活:穿笔挺的怀旧服装、听黑胶唱片、开敞篷卡迪拉克古董车、看好莱坞老电影。当然,这样窘困却惬意非常的生活仅存在童话里,用歌舞片表现再合适不过。情境为假,情绪佯真,观众便买账。
《爱乐之城》社会关联性不大,因个体情绪关联而获得年轻观众认同。这是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的个人主义的大众文化运作。这是针对个体的营销,是关于“你”和“我”、而非“你们”和“我们”的产品广告。尽管这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内部有认同,但仍不是“集体”,而是“有同质性”的个体的聚合:被好莱坞电影工业、娱乐产品长期规训而产生的高度一致的感官经验与反响。《爱乐之城》里男女主角都是单打独斗的独行侠。
“社群”观念是折损理想主义者尊严的:塞巴斯蒂安在Keith的“the messenger”乐队格格不入,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遗世独立姿态;米亚写的、表演的则是独角戏,跟她的三位室友毫无关系。极端的个人主义令他们成为彼此的障碍:有好感的异性相互取暖也是暂时的,他们终将享受成功者的孤独。对这些活在自我世界里的“追梦者”来说,他们的挫折是比贫困、战乱、天地宇宙还严重的“创伤”,他们全部的人间疾苦。
对身份政治的过度强调使得人们无法对自身经验之外的人和事产生共情,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对超越性同理心和正义感的阻碍。当然,“政治正确“话语不仅是空洞修辞,它是前辈正义之士奋斗出来的对少数族裔的起码尊重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的思想,纠正人的偏见,但也不可否认,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这样表现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良好教养,他们有时无法掩藏或深或浅或有意或无意的优越感。因为这套话语规训与他们的日常实践无关:由于阶层和种族隔离,只有少数人能真正接触到底层少数族裔、真正产生共情,就像大学里有些养尊处优的白人教授因研究黑人电影功成名就却在现实中远离黑人。我与几位白人男性学生探讨过另一部上中产白人男性中心视角的电影《海边的曼切斯特》(影片以中产理解写男性蓝领工人,女性角色全部是毫无深度的陪衬),发现他们对其中白人男性挫败感有很强认同感。成长经验不同,相信他们对《月光》就不如我那位同性恋同事共鸣深。由于电影制作需要大量资本的本性,非但主流商业电影,现今美国所谓低成本独立电影都被握有资源的人(多为白人男性)掌控,通常传达一种比较狭隘、自恋的视角与经验,在自身特权遭受威胁时、身处困境时,尤为如此。
在所谓白人身份危机时刻,商业产品更要强调白人男性的优点和权威,跟三十年代有某种呼应。在这很多人都感觉失落的美国多事之秋,回想本文开头提及的“被遗忘的人”:在学者霍莉·艾伦(Holly Allen)看来,“‘被遗忘的人’这一说法意味着失业的白人男性作为这精力充沛、富有男子气概的国家的善意无害的成员,‘新政’推崇白人男性为主导的家庭去抵消官方权力扩展的焦虑” 。八十多年后,我们又看到白人男性气质中的种族主义、性别沙文主义、宗教排他主义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体现,银幕上也不例外,《爱乐之城》这样的电影含蓄地告诉我们:金发碧眼是最美的,白人文化是高尚的,白人男性是能坚持理想并代表权威的,因为他们的音乐趣味是最好的、情感是最深邃的……
在电影院里为此感动的希拉里支持者,会有一丝“愧疚的快感”(guilty pleasure)吗?
抛开了一切的好评与差评,耐着心又把电影看了一遍。《La La Land》这部电影是拍给幼稚者的童话,成熟者的悲剧。La La Land。即一种极乐的、在梦境中一般的、脱离残酷现实的精神状态。
La La Land与其说是影片的名称,不如说它只是在解释电影最后那段华丽的蒙太奇。
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这部电影在最后那段蒙太奇结束后就已经结束了,悲伤又甜蜜,忍不住落泪。而在一部分人眼中,这部电影在蒙太奇结束,女主角起身对老公说“我们走吧。”时才刚刚开始。
“我想试着谈论一下:生活和艺术,梦想和现实,能怎样融合在一起。”这是导演达米安拍摄《爱乐之城》的初衷。不得不说达米安是个好导演,更是个好编剧。
达米安为生活与艺术的融合找到了最适合的方法——歌舞片。同时也为梦想和现实的融合想出了最合适的故事。
如果你说这部电影在讲爱情,真的错了。影片拍摄的初衷没有爱情这个词,尽管它和爱情擦了边,也只是擦了边。正是这个擦边在优秀的营销下影片让大部分人哭的稀里哗啦,俨然成了一部童话。
不讲爱情,它讲的是什么呢?梦想与现实。
影片从一开始就提示了我们,不同于《泰坦尼克号》中的杰克和罗丝社会地位的不同,《爱乐之城》里的米娅和塞巴除了同样处于人生低谷以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从何看出呢?电影开场的歌舞后,塞巴开着一辆美产老爷车,因为车载音响是磁带所以他在倒带,米娅开着日产丰田。如果你了解美国应该会知道,塞巴的老爷车象征着具有强烈浪漫主义情怀的艺术青年,而米娅的日产丰田,则是被誉为不具有“美国精神”的败类,典型的不讲情怀立场的实用主义者。
同样预示着这些的还有,米娅让塞巴帮忙拿车钥匙时,塞巴看到好多丰田钥匙不知道哪个是米娅的,米娅的钥匙专门系上了绿绳更加反映了米娅是个完完全全的实用主义者,她早已适应这样的生活。再加上后面米娅为了便宜选择合租公寓,塞巴即便没钱也要一个人住。其实从影片开头两人就被推上了对立面,同时也直接告诉了你影片的结局——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何为梦想?是米娅为了当演员面试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不是,在电影里挑起梦想这个担子的人我觉得是塞巴。那米娅呢?米娅是现实。
对于塞巴而言,做好音乐是他的梦想,就和所有爱音乐的人一样。可是从开头母亲和饭店老板的不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塞巴的生命中缺少的是一个理解他的人,米娅出现了。这就是一种梦想的体现。
对于米娅而言,自己虽然面试总是不过,但拥有着稳定的工作,甚至拥有着一个高富帅的男朋友。塞巴于她,反而更像是一个处境相同能聊得来的情人。这就是现实。
电影之后的发展也正如米娅和塞巴之间的复杂关系。米娅有意无意的暗示塞巴没有稳定的工作,塞巴终于下定决心加入了本不想加入的乐队,为了挣钱,为了他梦想中的爱情。米娅在台下看着塞巴成功,终于暴露了自己自私的那一面,以“没时间陪我”的理由与塞巴大闹一场,说到底这就是害怕塞巴先自己一步成功打破了两个人平等的关系,自己的自卑和没安全感造成的。毕竟,米娅是个实用主义者啊,你能为我所用你才是有价值的,这才是米娅的现实。
而塞巴呢?傻愣愣站在米娅家门口,用汽车喇叭威胁米娅坚持自己的梦想,逼着米娅抓住最后的机会飞往巴黎。你能成功便是我的骄傲,这就是塞巴的梦想。
电影最后,在镜头中我们看到了米娅的生活,没有一丝塞巴的痕迹。挽着老公手的样子反倒像是嫁入豪门的小麻雀。而在塞巴的生活中呢?米娅一直存在,从米娅设计的酒吧logo,到必经街角墙上米娅的巨幅海报,甚至于看见台下的米娅,于无言中d起那首两人相遇时的旋律。对塞巴而言,音乐和米娅就是梦想。
在美轮美奂的蒙太奇之后,幼稚者的童话终于结束了,成熟者的现实开始了。米娅起身“我们走吧。”让我想起了电影《楚门的世界》结尾。两个保安看着楚门消失在电视屏幕里,拿起遥控说“完了,看看还有什么节目。”。米娅就如同保安,塞巴又如同楚门,塞巴能为米娅带来的不过是回忆与幻想,结束了那段童话般的幻想后,一句“走吧”预示着米娅的现实生活回归。她不欠塞巴什么,塞巴也不欠她。这就是现实,比童话残酷的多。
导演达米安通过细节一边致敬了经典一边表现了电影中人物的性格。他不是在和你讲什么过家家的爱情,他在和你探讨爱情与面包你该选择哪个?生在现实或者死于梦想你选择哪个?
《爱乐之城》能拥有如此高的评价并获得这么多的奖项,不只是因为音乐和画面,还有故事的深度。达米安把一部电影的层次分得很明晰,就好像我之前所说的,这部电影是拍给幼稚者的童话,成熟者的悲剧。
爱乐之城观后感作文【1】当我得知期盼已久的《爱乐之城》在威尼斯赢得满堂彩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旅行的意义在于观光,但对于我来说,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仅仅是为了呼吸一下科罗拉多新鲜的空气(大麻味?……),以及在特柳赖德电影节抢先观看这部特立独行的电影罢了。
达米安•沙泽勒的前作《爆裂鼓手》相信影迷们再熟悉不过了。这部在我看来2014的最佳作品,虽不完美,却充满了火花和能量,甚至让人在观影后感到不自觉的亢奋。我还记得当年我先后6次进电影院跟不同的朋友去观看这部电影,就像是为了这剂会上瘾的兴奋剂一般。我大概只是需要去感受那最后20分钟的澎湃以及电影结束后观众们的热烈欢呼声吧?也正因为这样,我说走就走地去看《爱乐之城》,应该也只是希望沙泽勒能在这个羸弱的2016给我同样的那种兴奋剂般的感觉而已。
在特柳赖德上,《爱乐之城》毫无疑问地赢得了当时包括我在内所有在场观众的心,甚至在播放期间就收获两次欢呼。这部在威尼斯打响第一炮后回到美国的影片,看似反好莱坞,却又再好莱坞不过。它是那么的反好莱坞——没有任何原始素材的音乐剧在当今的大制作人手中几乎是不可能被搬上大荧幕的。谁让年轻人们都不怎么喜欢音乐剧呢,更何况就算有百老汇耳熟能详的歌曲作为铺垫的改编电影也不见得能做得多好,比如几年前的《悲惨世界》就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例子。所以编剧兼导演沙泽勒竟然能用6年的坚持把这么一部电影奉献给影迷们,实在是奇迹而又反好莱坞的一件事。但它又是一部再好莱坞不过的电影——镜头下华美的洛杉矶,俊俏得过分完美的男女主角,以及那甜美而苦涩的爱情故事,无不是好莱坞电影最让人熟悉不过的元素了。它是那么的好莱坞,以致于当那硕大而怀旧的圆体The End出现在荧幕中,当Made in Hollywood(好莱坞制作)毫不掩饰地出现在观众的眼前时,我一点都不觉得有违和感。
而这份好莱坞感,这份沙泽勒所极力营造的感觉,除了给我那期待已久、似乎在2016无法感受到的兴奋外,更多的还是一份感动。
爱乐之城观后感作文【2】金球奖、威尼斯电影节双影后艾玛·斯通在影片中饰演想当演员却郁郁不得志的咖啡馆前台女孩米娅,而金球奖影帝瑞恩·高斯林则饰演落魄爵士乐师的塞巴斯汀。二人偶遇之后,两颗寂寞的心灵因为梦想的共鸣而相知相爱,在各自追寻梦想的道路上互相鼓励。《爱乐之城》的导演达米恩在影片中巧妙地将四季的特点与主人公的`心情变化相结合,冬天认识,春天相爱,夏天热恋,秋天分手,5年后的冬天再次重逢,在大银幕上制造了情感四季。
然而,要梦想还是要爱情,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二人为了成全彼此的梦想不得不分手,走向各自的人生。尽管导演别出心裁地在结尾安排了一场想象中的五年后再相遇的画面,一首老歌和一个笑容,尤其是两人之间爱情萌动的那首曲子,无不催人泪下。但是心系彼此的他们依然是一对无法在一起的有情人。《爱乐之城》在爱情的基调上又探讨了梦想、奋斗和抉择,引发很多年轻人共鸣和思考。
歌舞片曾是好莱坞影片重要类型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鼎盛,《窈窕淑女》、《音乐之声》等卖座影片就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科幻片的兴起使得歌舞片逐渐衰落。导演达米恩·查泽雷力排众难,花费七年时间,终于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拍出一部致敬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现象大片。他认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在银幕上看到希望和浪漫,歌舞片能表达一些只有电影这种媒介才能表达的情绪。
《爱乐之城》歌舞表演是最大亮点,唯美的故事加上优质的声音和舞蹈,令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爱情歌舞片的迷人气质。影片中各种音乐类型层出不穷,从钢琴、爵士,到流行、音乐剧唱白,甚至当对白已显多余,音乐便成了最好的语言。几场舞蹈场面都拍得各有特色,特别是开场的群舞,以洛杉矶堵车的场面为背景,十分精彩。
爱乐之城观后感作文【3】《爱乐之城》自颁奖季以来屡屡获奖,在今年情人节档备受关注,影院经理们也感到欣慰。刘晖表示,情人节能有这样一部高品质的影片挺令人高兴,而且片子也确实争气,“《爱乐之城》白天的上座率就已经很高,达到70%至80%左右,到了晚上就达到九成。”
刘晖认为,《爱乐之城》有望突破好莱坞歌舞片在内地的瓶颈。过去好莱坞爱情片、歌舞片很少引进,即使引进了票房也不太好,此前的《悲惨世界》《纽约奇缘》《间谍同盟》都叫好不叫座。“正因为这个类型基础比较差,所以《爱乐之城》更容易有所突破。目前影片口碑这么好,又一直在拿奖,如果接下来再拿下奥斯卡奖,关注度会更高,有可能长线作战。”
蒋勇也持同样看法,认为《爱乐之城》会创下歌舞片内地票房新纪录。对于该片为何如此受欢迎,他分析,“应该说和影片获奖的关系挺大。因为奥斯卡获奖影片一般都是在颁奖典礼后才会引进,但这次《爱乐之城》在奥斯卡奖揭晓前两周就已经登陆内地。而且该片基本提前锁定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营销氛围很足,加上一轮轮点映下来的好口碑,票房好也不意外。”
但也有人并不看好《爱乐之城》未来的走势。在影评人云飞扬看来,评论界和社交媒体上对该片的吹捧有“叶公好龙”之嫌。“影片点映时,我坐在前排,特意回头看了看,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没什么明显的兴奋点,但出了影院一发朋友圈都嗨起来了。”他认为影片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化隔膜,能走多远还不好说。“虽然片子里的一个核心是爱情,但我感觉它作为爱情片的吸引力不够,还是更偏重于歌舞片。可中国有几个观众对百老汇、洛杉矶的歌舞感兴趣?能听懂爵士乐?听不懂也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懂,只能说好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