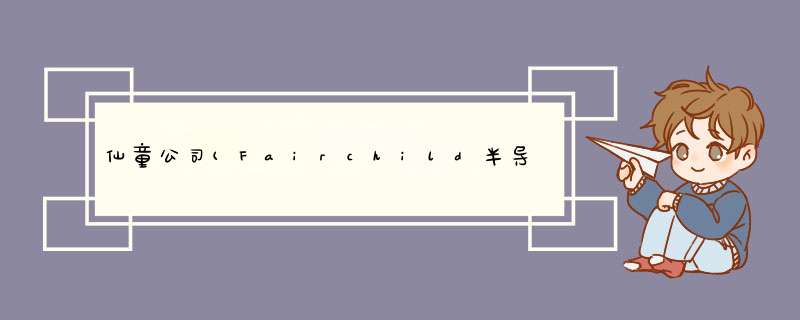
可惜,肖克利是天才的科学家,却缺乏经营能力;他雄心勃勃,但对管理一窍不通。特曼曾评论说:"肖克利在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眼里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他们又很难跟他共事。"一年之中,实验室没有研制出任何象样的产品。八位青年瞒着肖克利开始计划出走。在诺依斯带领下,他们向肖克利递交了辞职书。肖克利怒不可遏地骂他们是“八叛逆”(The Traitorous Eight)。青年人面面相觑,但还是义无反顾离开了那个让他们慕名而来,之后又相聚在一起的“伯乐”。不过,后来就连肖克利本人也改口把他们称为“八个天才的叛逆”。在硅谷许多著作书刊中,“八叛逆”的照片与惠普的车库照片属于同一级别,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
编辑本段发展历程诞生“八叛逆”找到了一家纽约的摄影器材公司来给他们投资创业,这家公司名称为Fairchild,音译“费尔柴尔德”,但通常意译为“仙童”。费尔柴尔德不仅是企业家,也是发明家。他的发明主要在航空领域,包括密封舱飞机、折叠机翼等等。由于产品非常畅销,他在1936年将公司一分为二,而其中生产照相机和电子设备的就是仙童摄影器材公司。当“八叛逆”向他寻求合作的时候,已经60多岁的费尔柴尔德先生仅仅给他们提供了3600美元的创业基金,要求他们开发和生产商业半导体器件,并享有两年的购买特权。于是,“八叛逆”创办的企业被正式命名为仙童半导体公司,“仙童”之首自然是诺依斯。1957年10月,仙童半导体公司在硅谷嘹望山查尔斯顿路租下一间小屋,距离肖克利实验室和距离当初惠普公司的汽车库差不多远。“仙童”们商议要制造一种双扩散基型晶体管,以便用硅来取代传统的锗材料,这是他们在肖克利实验室尚未完成却又不受肖克利重视的项目。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答应提供财力,总额为150万美元。诺依斯给伙伴们分了工,由赫尔尼和摩尔负责研究新的扩散工艺,而他自己则与拉斯特一起专攻平面照相技术。
发展1958年1月,蓝色巨人 IBM公司给了他们第一张订单,订购100个硅晶体管,用于该公司电脑的存储器。到1958年底,“八叛逆”的小小公司已经拥有50万销售额和100名员工,依靠技术创新的优势,一举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
仙童半导体公司在诺依斯精心运筹下,业务迅速地发展,同时,一整套制造晶体管的平面处理技术也日趋成熟。天才科学家赫尔尼是众"仙童"中的佼佼者,他像变魔术一般把硅表面的氧化层挤压到最大限度。仙童公司制造晶体管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们首先把具有半导体性质的杂质扩散到高纯度硅片上,然而在掩模上绘好晶体管结构,用照相制版的方法缩小,将结构显影在硅片表面氧化层,再用光刻法去掉不需要的部分。扩散、掩模、照相、光刻,整个过程叫做平面处理技术,它标志着硅晶体管批量生产的一大飞跃,也为"仙童"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大门,使他们看到了一个无底的深渊:用这种方法既然能做一个晶体管,为什么不能做它几十个、几百个,乃至成千上万呢?1959年1月23日,诺依斯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最伟大也被当时的人们看作是最疯狂的设想。
1959年2月,德克萨斯仪器公司(TI)工程师基尔比(J.kilby)申请第一个集成电路发明专利的消息传来,诺依斯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八叛逆”商议对策。基尔比在TI公司面临的难题,比如在硅片上进行两次扩散和导线互相连接等等,正是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拿手好戏。诺依斯提出:可以用蒸发沉积金属的方法代替热焊接导线,这是解决元件相互连接的最好途径。仙童半导体公司开始奋起疾追。1959年7月30日,他们也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为争夺集成电路的发明权,两家公司开始旷日持久的争执。1966年,基尔比和诺依斯同时被富兰克林学会授予“巴兰丁”奖章,基尔比被誉为“第一块集成电路的发明家”,而诺依斯被誉为“提出了适合于工业生产的集成电路理论”的人。1969年,法院最后的判决下达,也从法律上实际承认了集成电路是一项同时的发明。
1960年,仙童半导体公司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功。由于发明集成电路使它的名声大振,母公司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决定以300万美元购买其股权,“八叛逆”每人拥有了价值25万美元的股票。1964年,仙童半导体公司创始人之一摩尔博士,以三页纸的短小篇幅,发表了一个奇特的定律。摩尔天才地预言说道,集成电路上能被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将会以每18个月翻一番的速度稳定增长,并在今后数十年内保持着这种势头。摩尔所作的这个预言,因后来集成电路的发展而得以证明,并在较长时期保持了它的有效性,被人誉为“摩尔定律”,成为IT产业的“ 第一定律”。
没落60年代的仙童半导体公司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到1967年,公司营业额已接近2亿美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据那一年进入该公司的虞有澄博士(现英特尔公司华裔副总裁)回忆说:“进入仙童公司,就等于跨进了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大门。”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仙童公司也开始孕育着危机。母公司总经理不断把利润转移到东海岸,去支持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的盈利水平。在目睹了母公司的不公平之后,“八叛逆”中的赫尔尼、罗伯茨和克莱尔首先负气出走,成立了阿内尔科公司。据说,赫尔尼后来创办的新公司达12家之多。随后,“八叛逆”另一成员格拉斯也带着几个人脱离仙童创办西格奈蒂克斯半导体公司。从此,纷纷涌进仙童的大批人才精英,又纷纷出走自行创业。结果人才纷纷离仙童而去,最终仙童中的斯波克将NSC弄成了全球第六大半导体厂商,桑德斯创立了AMD,而诺依斯和摩尔则创立了INTEL(英特尔),而这就是仙童的整个历程。[1]
编辑本段公司影响“仙童”,一个永远让世人铭记和仰慕的名字,一个对半导体界乃至全世界作出了后人无法企及的贡献。引用苹果总裁乔布斯的一句话:“仙童半导体公司就象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仙童半导体拥有与众不同的晶体管制作方式,扩散、掩模、照相、光刻,整个过程叫做平面处理技术,它标志着硅晶体管批量生产的一大飞跃。在1969年的半导体工程师大会,400位与会者中只有24位的履历表上没有在仙童公司的工作的经历。
你很难想象我国的芯片产业走得有多艰难!
30年前,日本芯片全球占有率高达53%,美国仅37%,这辉煌让美国愤怒,美国将日本按在地上摩擦,逼迫日本连续签订两次不平等半导体条约,内部核心资料全被美国中情局带走。日本用22年时间,举国之力发展起来的支柱产业,就这样被美国搞垮了,经济被拖入泥沼,永无翻身可能。
类似的拙劣行径,美国人正在故伎重施,一系列所谓“制裁”正发生在华为、中芯国际等民族企业身上!
2019年5月15日,美国一纸禁令,限制美国企业为华为提供零部件和服务。时隔一年,第二轮“追杀令”升级,只要是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企业,任何一家都不准为华为制造芯片,自此彻底掐断了华为的芯片代工之路。
作为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中芯国际早在2018年便耗资1.2亿美元从ASML定制了一台EUV光刻机,而美国却从中作梗,限制相关设备出口我国,时隔4年,这台光刻机才有机会交付。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面对美国封锁,我们势必要走出一条产业自强之路!
也恰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群 科技 志士前赴后继,毅然决然踏上这条“中国芯”振兴之路。
一、中国半导体教父——张汝京
他,年少留学国外,学成后毅然归国报效中华。五次创业,被陷害,再重来,凭借一己之力把中国送进尖端芯片 科技 赛道,他就是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
1997年张汝京离开最顶尖的芯片制造企业——德州仪器,回到中国开始创业。短短3年时间,势头直逼台积电。台积电坐不住了,利用关系收购了张汝京的公司。之后,张汝京又在中国香港注册了一家新公司——中芯国际。
这次,张汝京不仅从台湾带回300骨干,还像传教士一样,横穿美国东西两岸宣讲,召唤了100多位在美华人回国。他深知,在中国半导体产业,人才比资金更紧缺。
中芯国际用3年时间,将大陆芯片水平拉快了30年。
商场如战场,2002年,中国台湾向发送了撤资警告,否则就要赔款1500万台币。张汝京不予理会。气急败坏的台湾当局撤销了张汝京的台湾户籍,甚至把他列入通缉名单。
你方唱罢我登场,台积电也闻讯杀了过来,下手更狠。张汝京被迫离开中芯国际,还签下3年内不能从事芯片工作的竞业协议。离开的那一天,张汝京在厂区来回转悠了3小时,看着9年来为之付出一切的一草一木,心里五味杂陈,最后对着送行的工人说了三个字“别趴下”
3年期满,张汝京开着10年前那辆破旧的白色福特,再次回到芯片行业。中国芯片产业在他的带领下,已经完成了从低端到高端的跨越。这次,他转移了目光,将个人精力投向中国芯片的另一个弱项——“硅”元素。
当产能达到12万片每月后,张汝京将公司交给了国资的上海硅产业,继续奔赴另一个赛道——IDM。
2017年,倪光南院士代表国家,为张汝京颁发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终身贡献奖。
二、芯片届的“堂吉诃德”——倪光南
倪光南,1939年出生。大学毕业时,以脉冲编码通讯为题,写出极其创新的观点,震惊导师。1981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寄来邀请,倪光南待了两年就回国了,拎着他自掏腰包购买的核心机器和电路芯片。要知道,彼时他在加拿大的年薪是4.3万加元,比国内工资高出整整70倍。
面对家人朋友的不理解,倪光南说:“如果我不回来,此后我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
1984年,一个商人敲响了倪光南的门,这个人就是柳传志。科学家和商人最大的区别是,一个终身立志振兴中国 科技 ,一个只想赚钱。
1985年,第一期联想式汉卡成功研发并投入市场,倪光南先后更新了8个型号,成为公司的核心技术。直到1994年,联想从一个初始资金只有20万的小公司,变成销售额高达47.3亿元的龙头企业。
极具前瞻性的倪光南主张由联想公司牵头,成立国家投资计划,研究中国自主制造芯片技术,但身为商人的柳传志不愿冒这个险,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1995年6月,柳传志决定放弃这颗“ 科技 棋子”,着手市场贸易。董事会当场宣布解除倪光南的一切职务,柳传志说得声泪俱下,感谢倪光南的付出,却绝口不提让倪光南留下。倪光南被迫离开后,他主持的一系列中国自主研发芯片计划也被迫叫停。
时至今日,全球芯片市场风云变幻,我们也看懂了倪光南的目光深远。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天的联想和中国半导体产业,又会如何?
为了中国芯片,倪光南没日没夜奔走,82岁高龄的他,租住在北京的房子里,身边没有人照顾,只有他挚爱的科研相伴。一年超过300天沉浸在科研中,节假日都舍不得休息。
当被问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倪光南答到:“发现自己帮不上别人忙的时候”
三、芯片奇才——梁孟松
玩技术的人都有瘾。梁孟松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大佬,深耕半导体行业35年,取得四百多项发明专利。有人说他是半导体领域的科研狂人,而老东家却视他为“投奔敌营的叛将”。
从台积电到三星,再到中芯国际,每一次跳槽都引起业界震动;不仅改变了入职企业的发展轨迹,更是凭一己之力牵动着整个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
梁孟松在中芯国际上任后,开启了一系列猛虎 *** 作。不到一年时间,将28nm制程的良品率从60%提升至85%以上;2019年,将14nm制程正式量产,良品率从3%飙升到95%以上;一年后,28nm、14nm、12nm,以及N+1技术均已进入规模量产;7nm技术的开发已经完成,5nm和3nm技术也在有序展开。
在梁孟松的带领下,中芯国际用3年时间走完台积电10年的路。
美团王兴CEO曾对梁孟松表达过敬意:“梁孟松先生将中芯国际的全部收入,分文未取,全部捐给了中国的教育基金会,不为挣钱,就是要争一口气,牛!”
我们将梁孟松的职业生涯摊开了看,会发现他的目标非常清晰,无关金钱无关职位,从始至终他想要的东西就只有一个——高端芯片开发项目的主导权。
四、中国 科技 界、政治界的双重战士——江上舟
江上舟的履历跟前几位不太一样,他四十岁完成博士学位,回国进入仕途,执政期间成绩斐然,一直身兼数职超负荷工作,朱镕基同志曾对他说:“将3万多搬迁农民安置好,你要白一半头发”。曾任三亚市副市长,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副秘书长等,是当时执政官员中少有的懂半导体的。
作为一名战略型科学家,他想的从来不是走哪一步,他下的是一整盘棋。
说到江上舟,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张汝京。当年邀请张汝京到上海来建厂的人就是江上舟。2000年,张汝京带领300名半导体工程师来到上海,中芯国际就此成立。后来,台积电开始起诉中芯国际,纠缠不清的官司让中芯国际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濒临破产。
2009年,张汝京被迫出局,江上舟放弃政府身份,临危受命,成为中芯国际董事长。此时的江上舟已经患癌7年,他的身体早已不允许他承担如此繁重高压的工作,但江上舟还是义无反顾挑起了这个担子。很快,中芯国际由亏损转到盈利,甚至还有能力收购武汉新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2011年6月27日,江上舟因肺癌去世,生命永远停在64岁。去世前一周,他还在用手机主持董事会。
五、中国芯片 历史 上“最强猎头”——俞忠钰
俞忠钰,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半导体专家。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问题所在。当年他带队去国外顶尖的芯片制造公司——德州仪器考察,在接待团队清一色的外国人当中,欣喜地发现了一张中国面孔,这个中国小伙就是张汝京。
当时的中国半导体行业百废待兴,临走时俞忠钰专门拉着张汝京的手,给了他一封口头offer,“我们在北京等你!”
这一句话,改写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写了整个中国芯片史的命运。
六、“芯”时代的扫地僧——邱慈云
从1984年到1996年,邱慈云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整整12年。贝尔实验室是这个世界上培育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研究机构,邱慈云的离开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2001年在张汝京的邀请下,他加入中芯国际,开始了半导体事业。相比于CEO身份,邱慈云更像一位研究员。他说话谦逊,语气平和,但这些都难以掩盖他在半导体产业取得的突出成绩。
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邱慈云曾经带领华虹NEC、马来西亚Silterra、中芯国际三家公司扭亏为盈,2019年,他出任上海新升CEO,带领其走向新征途。
邱慈云为人低调,网上关于他的个人报道几乎为零。
74岁的张汝京、82岁的倪光南、70岁的梁孟松、64岁的俞忠钰、66岁的邱慈云,还有生命永远定格在64岁的江上舟,他们都是“中国芯”振兴之路上的播种者。他们是灯塔,是火炬。
这群民族战士,生在中国最穷困的时代,却放弃优渥生活,毅然决然报效祖国。就算伤痕累累,头发花白,也要为“中国芯”战斗到底。我们正在穿越一条隧道,走下去,曙光就在前方。
数以万计的中国芯片人接过这簇火苗,立志让中国芯的光辉照亮华夏每一寸山河!
谨以此文致敬为复兴中华做出努力的每一位中国芯片人。
这里是,关注我,一起做快乐且自信的中国人~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