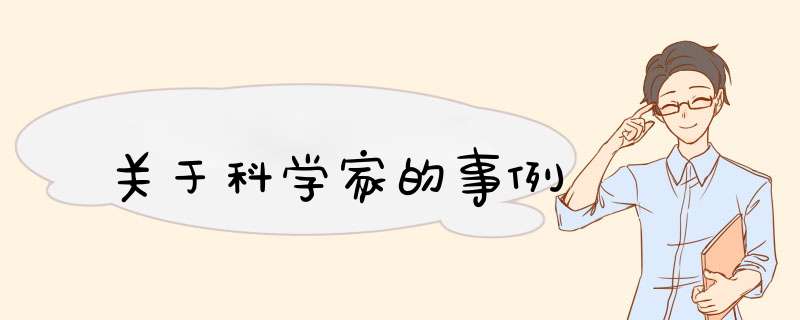
物理学家牛顿小时候看到苹果熟了,掉下来很好奇,他想,地球上的东西,失去了支持后为什么都掉到地上来,而不会向其它方向掉呢?后来,他终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爱迪生
爱迪生小时候对什么都感兴趣。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总想试一试,弄个明白。有一次他看见花园的篱笆边有一个野蜂窝,感到很奇怪,就用棍子去拨,想看个究竟,结果脸被野蜂蜇得肿了起来,他还是不甘心,非看清楚蜂窝的构造才行。爱迪生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发明家。
哥白尼
哥白尼慑于教会的统治,怕遭到反对和迫害,迟迟不愿将《天体运行论》公开出版。1543年5月24日,哥白尼在他弥留之际,才在病榻上见到了刚刚出版的《天体运行论》样书。
尽管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公布后,受到社会上宗教势力和守旧的人们的污蔑和攻击,甚至于信仰宣传这一学说的人也被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但是哥白尼的学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哥白尼和他的《天体运行论》就像是黑暗夜空中闪烁的巨星,一直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爱因斯坦
一个12岁的孩子,在不可思议的感受中迷上了数学,而且初次领略了一个古老又永恒的哲学命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个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平方相加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个平方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却能证明。人的思维能证明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这是多么奇妙!那么量一量行不行呢?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小爱因斯坦当时是否作过这样的设想。从上边引证的自述来看,爱因斯坦直觉地感到:不行。一千次、一万次量度不能代替一次证明,一次证明却能代替一千次、一万次量度。几何学给爱因斯坦带来的思维奇妙性,使他来不及按部就班,竟一口气把《圣明几何学小书》学到最后一页。 在爱因斯坦步入自然科学领域的最初几步,有两个人是很重要的,虽然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思想上对爱因斯坦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正是他们,把打开自然科学殿堂大门的第一把钥匙递给了爱因斯坦。这两个人是爱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爱因斯坦和来自俄国的大学生塔尔梅。 雅各布·爱因斯坦是个很有事业心并且精力充沛的人,是一个工程师,也和赫尔曼·爱因斯坦一样爱好数学,就是他动员赫尔曼·爱因斯坦一家移居慕尼黑。在工厂里,他管技术;在家里,他则是小爱因斯坦入学前的数学启蒙者。爱因斯坦上学后,雅各布叔叔常常给小爱因斯坦出些数学题让他解答。每当正确解答后,爱因斯坦就特别高兴。 1888年10月,爱因斯坦从慕尼黑国民学校进入路易波尔德中学学习,一直读到15岁。这期间,来自俄国的大学生塔尔梅成为爱因斯坦家里的常客。塔尔梅每星期四到爱因斯坦家来吃晚饭,这是慕尼黑犹太人帮助外国来的穷苦犹太学生的慈善行动。塔尔梅是学医的,但对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哲学均抱有兴趣。他对小爱因斯坦的超常求知欲及能力很吃惊。那本让爱因斯坦终身难忘的“神圣的几何小书”便是塔尔梅送给爱因斯坦的。一开始,塔尔梅总是和爱因斯坦谈论数学问题,越谈就越引起爱因斯坦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对学校枯燥教学方式厌倦的爱因斯坦干脆自学起微积分,他提出的数学问题常弄得中学数学老师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 尽管爱因斯坦的数学成绩永远第一,但老师并不喜欢他。 一次,一个老师公开对他说:“如果你不在我的班上,我会愉快得多。”爱因斯坦不解地回答:“我并没有做什么错事呀!”老师回答说:“对,确是这样。可你老在后排笑着,这就亵渎了教师需要在班级中得到的尊敬感。” 爱因斯坦当然没有任何过错,他的老师的抱怨也可理解。爱因斯坦超常的数学能力确实让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感到难堪和无法言说的心理压力。 和这位教师不太大度的心理相反,塔尔梅虽不久后也不是爱因斯坦数学上的对手了,但他依然热情地为爱因斯坦介绍当时流行的种种自然科学书籍和康德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布赫纳的《力和物质》、伯恩斯坦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给爱因斯坦留下极深的印象。在伟大的科学家们的生涯中,人们发现:他们往往在年幼时期由于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一部著作,从而对他们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爱因斯坦也不例外,他在《自述》中说: “在12—16岁的时候,我熟悉了基础数学,包括微积分原理。这时,我幸运地接触到一些书,它们在逻辑严密性方面并不太严格,但是能够简单明了地突出基本思想。总的说来,这个学习确实是令人神往的;它给我的印象之深并不亚于初等几何,好几次达到了顶点——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无穷级数,微分和积分概念。我还幸运地从一部卓越的通俗读物中知道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这部著作①几乎完全局限于定性的叙述,这是一部我聚精会神地阅读了的著作。当我17岁那年作为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学生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时,我已经学过一些理论物理学了
华罗庚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全家悄然登上一条不大的邮船,离开生活了4年的美国。当他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电波播送了他的《告美国同学的公开信》。信中激情洋溢地写道:“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
华罗庚又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数学系主任。不久,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百倍珍惜党和国家为科学研究提供的大好时光。他白天拄着拐杖到学校讲课,晚上以案板当书桌,在灯下从事数学研究,常常写作到深夜。有时,为了求证一个问题,他常常深夜从床上爬起,顺手拿起床头的报纸,在四周的空白处进行演算和论证。在他的屋里,桌上、床上、地上,到处都堆满了演算稿纸。他用毅力与勤奋,编织出成功和荣誉。
1956年,他的重要论文《典型域上的调合分析》,荣获中国科学院第一批科学奖金的一等奖。随后,他的长达60万字的巨著《数论导引》问世了。这部著作,倾注了他多年的心血。国内外的数学界为之震动了。他带领的数学研究所,也已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了。他们为征服解析数论、代数数论、涵数数论、泛涵分析、几何拓扑学等不同学科,已经扬帆起航,并各有卓越的建树。震撼世界的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个突出成果。
1979年12月,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新华社记者访问了他,问他回国以后的计划和打算。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了以下一段话:“在我几十年从事数学研究的生涯中,我最深的体会是,科学的根本是实。我虽然年近古稀,但仍以此告诫自己。”他沉默片刻又说:“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是我对自己的鞭策,也可以说是我今后的打算吧。”
“一辈子从实以终”,这种精神实在令后人钦佩!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