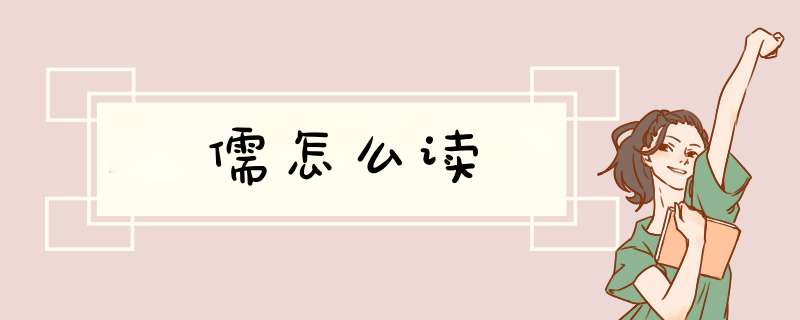
儒家的来源是设么?如何看孔子所说的“君子儒”和“小人儒”?儒家最初是一种职业,主要从事丧礼祭祀等事情,用当时看不起儒家的思想家墨子的话说,就是发死人财的人。
齐国著名宰相晏子曾经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有四种毛病。
这是当时儒者的通病,并不是针对孔子个人。
也就是说,不是孔子害了儒者,而是儒者害了孔子。
孔子年轻时候确实干过儒者主持丧礼的活,但那只是他的谋生手段而已,志当存高远的孔子,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者了。
那么儒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为什么惹得人品不错的晏宰相,对他们有那么大的意见呢?中国人历来重视丧葬礼仪,这些礼仪纷繁复杂、规矩很多,普通人不容易掌握。
按照现代经济学“有需求就有市场”的原理,当时丧葬礼仪的需求十分突出,就催生了特殊的社会阶层——“儒”,他们以专门替人 *** 办冠、丧、嫁、娶等礼仪为生。
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看人脸色,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
所以《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
为了保证自己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儒者提倡厚葬的观念,教人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搞一场体面的葬礼。
就像证券商劝人赶紧趁着牛市炒股,地产商让人涨价前赶紧买房一样,他们的一言一行渗透着利益。
和孔子一个时代的墨子先生,极度厌恶儒者的这种行为,作为儒家学派最激烈的反对者,他语带讽刺地说,“富人有丧,乃大悦,曰:此衣食之端也”,意思是,“太好了,那边富人家死人了,我们又有吃有喝了”。
所以,当时儒者给社会的印象很糟糕,他们是发死人财、骗吃骗喝的一群格调不高的小人。
孔子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者了。
他不是那种看见别人家死人就喜形于色的人。
给别人办丧事的时候,看到别人哭,他也跟着流泪,一天都吃不下饭。
孔子特别喜欢唱歌,但他一听到别人哭就跟着哭,只要这一天他哭过,他就不再唱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个富有同情心、多愁善感的“暖男”。
孔子也认识到,这些骗吃骗喝的儒者,就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孔子曾经教育弟子子夏,要做君子一样的儒者,别去做小人一样的儒者。
由此说明,孔子不仅自己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儒者割裂开来,而且要求自己的弟子们,不要做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了。
那么,“君子儒”和“小人儒”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君子儒”是指那些心底光明、道德修养极高的人,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更关心普天下人们的命运。
用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言,就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君子。
而“小人儒”的目标就是活着,没有道德理想,只关心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用著名歌剧《白毛女》里面的黄世仁的话,就是“我家自有粮满仓,哪管那穷人饿肚肠”。
儒,是柔弱、微小的意思。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
”相对于浩瀚的宇宙、无尽的时空,人无疑是极其脆弱与微不足道的。
然而,人又是这个宇宙中最神奇、最了不起的存在——因为人是有思想的,“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
”能够从这两个方面深入地去了解、认知自我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地方。
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却能够征服、驾驭、掌控世界上最强大东西,可以摧毁、消灭、粉碎天下最坚不可摧的事物。
儒,肯定包涵了这样的认知,看似柔弱微小的个体却可以驾驭比自己强悍庞大得多的东西——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赞叹道:“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
”天地之间能够主宰支配万物、领导管理大众的除了人类自己,还有什么物类能够做得到呢?不是“人力”又是什么呢?太史公的意思是除了领袖人物个人的杰出才能、非凡努力之外,更应该感谢无数杰出的先贤圣哲们——感谢他们在混沌无序、杂乱无章的世界里不断摸索、探寻、总结、制定出可以“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有效方法、不朽的制度:也就是“礼”。
后人们继承、借鉴于先祖粲然的文明成果和伟大的创举就可以便捷地役使群众、宰制万物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又是继承与发扬的意思。
儒家是最重视、崇拜先祖及其文明成果的,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最好的例证。
因此,儒家学说的最主要的部分应该不是自己独创的,而是经过精心筛选、仔细甄别后继承来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前人的伟岸、光辉,使孔子及其后学们坚信:天地无穷无尽,人与之相比微不足道。
但是只有人可以与天地相提并论、相并立——《中庸》里面说“唯天下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特别重视“仁”——仁者,人也。
就是赞扬人性中高尚、伟岸的部分,肯定人类难以估量的创造力和无尽的智慧、非凡的勇气。
儒,是关爱与敬意的代名词。
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暖的是母爱,而母爱又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东西——当幼仔的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母爱的强悍表现会让世界都为之颤栗、发抖。
儒家同样是二者兼具的,只是儒家更加强调关爱与互敬(原则性)的结合统一,而不是一味的溺爱。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即便是“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也有温情脉脉、柔情似水的一面。
这个世界不总是需要强悍霸气、大义凛然,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尽管不失威严却应该是一副温和从容的模样,让人喜欢靠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既然人可以同天地相并立,在帝王、诸侯、权贵们的面前为什么要奴颜婢膝、战战兢兢呢?完全可以不亢不卑、分庭抗礼的,相互间保持必要的尊重就可以相处,否则就离开。
同样的道理,所谓的强者有什么资格在弱者面前飞扬跋扈、骄纵恣肆呢?让弱者可以不亢不卑、分庭抗礼,拥有与帝王、权贵相对等的尊严——使每个人都懂得并且拥有自尊、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尊的同时应该给予他人相对应的尊重才是“礼”的实质、“敬”的主旨:越是高高在上的越应该谦恭温和、礼贤下士。
尤其是在对待弱小者、对待“鳏、寡、孤、独、废疾者”应该更加体恤恭敬、满怀同情与关爱——这是儒家修身的第一要务:自信而不狂妄,自尊而不骄横。
君子周而不比,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要让所有人都能够过上自尊、体面的生活,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是儒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践踏他人尊严的行径儒者会像母亲呵护幼崽的生命一样表现强悍,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
儒,是黑暗里的灯塔与火把,意味着坚强的引领、积极的探索和勇敢的尝试。
给人们以希望与期待。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人类的始祖在远古之时未必不是生活在这样严酷难破的“铁房子”里,力不如牛、奔不如马。
除了上天给予的肉体身躯,别无长物。
狼虫虎豹、蛇蝎毒虫、山火洪水、瘴气瘟疫……什么都致命、处处是壁垒。
在这样近乎决绝的生存环境里面如果没有了“希望”的指引、勇敢的尝试、积极的探索,今天的人类可能依然还处于蒙昧、未开化的状态。
《庄子·天运》里借助老子的口吻来规劝孔子“天鹅不是因为天天沐浴才毛色洁白,乌鸦也不是每天用黑色渍染才毛色乌黑,乌鸦的黑和天鹅的白都是出于本然,不可以人为的观点来评判高低、加以改变……”道家的观点无疑是深刻、透彻的,孔子并不是不知道、没有想过。
只不过要是依从道家那消极退避的观点的话,大禹还有必要去治水吗?提着极其简陋的工具、累得像个劳改犯一样,去对付那滔天的洪水?在那个年代里,是不是很疯狂?是不是自不量力?那么多的先贤圣哲还有必要在反复的失败之后又勇敢地去尝试、探索、努力奋斗吗?以柔弱之身、脆弱之体想要去驯服惊涛骇浪、汹涌洪水——与孔子以一己之力周游列国、推行王道仁政有什么不同呢?即使不成功,也要去尝试、去力行——为天下苍生计、为万世后人计,虽千万人吾往矣。
纵然是四处碰壁、连遭灾殃、备受打击,却矢志不渝、永不言弃——“当仁不让”,因为这是“儒”无法推卸与逃避的责任和担当。
至于后世用以愚民、钳制思想、维护统治的所谓的“儒家”,则是被肢解分割、强行改造过的“儒”——虽然他们敬奉孔子、祖述尧舜,但是与孔子的主张、儒家的宗旨已是大相径庭、天壤之别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