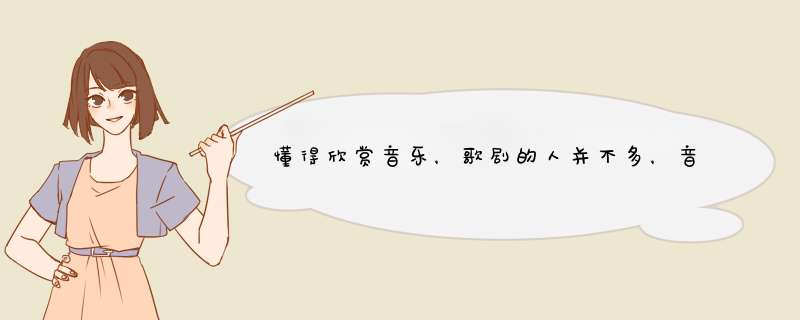
歌剧音乐剧,在中国被定义为小众,是因为市场受众不广,人们很难自发的进入音乐会场去听一场歌剧或者音乐剧。这也是由于当代的社会节奏比较快捷,人们无法静下心来,去欣赏一个另类的音乐作品。
之所以说它另类,是因为歌剧音乐剧不具有其他大众文化或者是网络文化以及电视文化所特殊的普及功能。如果说戏曲已经边缘成小众化,但是在中国仍有很浓厚的传统市场与心理氛围,那么从西方传过来的歌剧和音乐剧,
要在人们心理上认同和唤起,则需要很大的力量但实际上,当代的歌剧和音乐剧,也并非是濒临凋萎。相反它的市场份额逐步的在扩大,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愿意花一定的时间去接触高雅的音乐。
那么这也就说明了,歌剧和音乐剧并非是云山雾罩的。那么在推广和传播方面仍旧需要有所作为。其实以后的粉丝都非常具有深度和稳固性,那么如何吸引一批年轻的粉丝坐到剧院里面来,这才是重中之重。
只要他们进来了,高品质的歌剧和音乐剧,因为有着其他音乐载体无法比拟的深度和广度,一定会获得口碑和宣传。那么也就是在营销方面要多做努力。
比如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和心理,多发放一些关于音乐方面的调查,甚至可以做一些专业的APP来吸引这些音乐爱好者。稳定的粉丝,是任何艺术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基础。
应该利用好一切现代化的宣传工具,整合音乐歌剧的资源,做好相关的宣传和营销,获得稳定的粉丝,然后以有质量的演出获得认同和持续。
这些年看过的音乐剧,不提网上视频版的,光是现场版的就已有数十部。上海这座坐拥国内经济命脉的一线城市,有着小城市不曾拥有的五光十色和光怪陆离,也占尽了国际大都市该有的天时地利。也许这种繁荣是虚假的,但倒也真的,让音乐剧这颗弱不禁风的西洋苗子,有了蓬勃发展的一线生机。
我第一次看音乐剧是在2014年,看的是经本地化改良版的《Q大道》。音乐剧的内容非常风趣接地气,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何为音乐剧,以为看的是一部普通的话剧,也不知道剧院中途不能拍照的规矩,甚至在演员走到身边近距离表演时,拿出了手机为他拍照。若干年后我意外地发现,当时站在身边的那位演员就是《今夜百乐门》里的张海宇。
如今我已不再会做初入剧院时那些不懂规矩的事。站在一个入坑多年的“老人”角度,也更容易辨识出哪些是初入剧院的人。我记得2014年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看了人生的第二部音乐剧——《剧院魅影》。文化广场打着”暌违10年“的名头,吸引来了沪上众多的追求高雅艺术的文艺爱好者。而真正的音乐剧爱好者告诉我,其实那年距离《剧院魅影》首次来沪仅仅是第9年。为了能让艺术得到推广,剧院方也难免用了投机的营销策略。
第一次去文广看《剧院魅影》时,我见到一个戴着高高的蓝色礼帽、西装笔挺、打着礼结的年轻男人,样子有点像柯南。他的“正式”反倒凸显了他的“外行”,其实看音乐剧并不需要盛装出席。很多国人依然分不清音乐剧和歌剧的差别,一听我说喜欢看音乐剧,就联想到晦涩难懂、让人听着犯困的歌剧,觉得我兴趣高雅。且不说,真正的歌剧是否真的令人发困,起码音乐剧在英、美等国家是像电影一样司空见惯的娱乐项目。
区分音乐剧和歌剧最简单的方式就看演员戴不戴麦克风。歌剧演员通常不佩戴麦克风,视频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隐藏在发际的头麦也只是起收音的作用。要倚靠纯人声在剧院里回响的歌剧,在演员的演唱技巧上要求相当高,因此在舞蹈和表演上就相对没有音乐剧那么丰富,不太会出现演员载歌载舞的情景。而音乐剧更多元,题材也更丰富。演唱的要求虽没有歌剧演员那样高,但相对在跳和演的功底上,就需要均衡发展了。
2018年年末的最后10天里,我去剧院看了3部音乐剧——《卡门·古巴》、《乱世佳人》、《芝加哥》。这三部中,只有一部《芝加哥》来自百老汇。前阵子网上很火的《天朝渣男图鉴》就是以它为原型,进行的本地化创作。不过不同于本土版的辛辣和残酷,《芝加哥》更具有社会讽刺意味。《天朝渣男图鉴》里的每一个渣男似乎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而《芝加哥》中的女囚犯们上演的则是一场为自己的罪有应得而脱罪的说辞。巧舌如簧的律师为罪犯精心设计人设,利用社会舆论,煽动民众情绪,将加害者成功打造成“受害人”,为一个个死刑犯脱罪,而真正坐了冤狱的囚犯却被破例执行了死刑……运用眼泪、受害人的身份、悲惨的身世来博取大众的同情,来掩盖真正应该被视为核心的问题,潜移默化地引导观众的思维,引导舆论导向……这样的戏码在当下的中国不正在上演着么?只是这样的伎俩在40年前就被美国人识破,并改编成了音乐剧公开巡演,所以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真的仅仅是在楼房的精美、人均财富上吗?我们肉眼所无法察觉的差距比我们能感受到的要大得多。
《芝加哥》我是在美琪大剧院看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看的是谢君豪的《南海十三郎》,这是我看过的为数不多的几部话剧。美琪和上海文化广场相比,要老旧很多,位置的高度也不太合理,以至于看《芝加哥》的时候不断被前排观众挡住视线,不得不将身体坐得笔直,这又难免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而上海文化广场也有不足之处。坐在三楼观众席的话,舞台背景墙顶部的部分会被投光灯挡住,如果是需要配合背景来讲述故事情节的剧目,就很容易受影响。比如《伊丽莎白》中有几幕场景,死神需要从舞台右上方利刃形状的阶梯上下来,坐在后排的用户很难发现死神的存在,也许也无法察觉这楼梯设计成悬挂在SiSi顶部的利刃的样子,是暗示她的被刺结局的伏笔。
从视频里看音乐剧,画面和声音都清晰无比,只是音乐剧的魅力,不去现场看看只能体会到其一。音乐剧是一种能让人深切感觉到自己“活着”的演出。演员们这样跳啊唱啊,永远激情满满,好像永远不知疲倦的样子,是极具感染力的,以至于每次看音乐剧,我都有种变年轻的感觉,好像自己的血液也合着韵律跳动、沸腾,仿佛被人打了一针鸡血,变得容光焕发。
我记得我有段时间看了很多宝冢音乐剧。宝冢有个很有名的男役叫作大和悠河。我在视频里看她的演出时,觉得她毫无演技,演所有角色都是一副小流氓的样子。然后当她来上海演出,亲眼感受她现场的唱功和台风后,我终于知道宝冢演员为何在日本拥有如此崇高的社会地位,她们的确拥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当大和悠河扮演的夜礼服假面一袭黑色燕尾礼服,腰板挺直地站在舞台中央,你很容易将她和其他演员区分开来。她潇洒地将斗篷一甩,二话不说冲下舞台,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这样的台风引起了台下漫迷的阵阵尖叫。我虽不是漫迷,也不是大和悠河的粉丝,但那刻也深刻体会到宝冢另一位著名的男役——水夏希说过的话:宝冢的演员比男人更有男人味,比女人更有女人味。那天的大和悠河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出了剧院整个人还是陶醉的状态,好像见了什么心仪的明星偶像。我也终于体会到视频和现场的巨大差异。
其实真正高质量的音乐剧,未必在国内卖得很好。相反,一些由世界名著或是电影改编的,就经常能收获个盆满钵满。我记得去年我买了法国版《悲惨世界》,由于记错时间,晚去了一天,所以只能直接在现场等着黄牛有适合价格的余票卖给我。没想到,网上溢价几十块的票,到了现场直接翻了6倍的价格。即使是开场后,黄牛也丝毫不松口,这让我大开眼界。
上海文化广场门口似乎是外地的黄牛比较多,而美琪门口更多的是本地黄牛。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向外地黄牛问价。因为他们虽然要价狠,但态度还算温和,以中年女性或者年轻男性居多。而上海的黄牛大多是些穿着花衬衫戴着金链条的爷叔。他们是没来过上海的外地人印象中典型的上海人,有着小说里老上海人的精明和油滑。我不喜欢他们泛着油光的那脸横肉,也不喜欢他们挂钟式左右摇摆的身躯;不喜欢他们吞云吐雾又夸夸其谈,更不喜欢他们和我交易时的刻不容缓、不由分说。往往我还没明白发生什么,一笔交易就已经完成了。他们验票和点钞的手势都特别的老练、迅速,这节奏太快,和这座城市一样。你可以说,他们是这座洋气大都市的蛇虫鼠蚁,但他们恰恰也是这座城市最具生命力的个体。
剧院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由于身边喜欢音乐剧的人不多,我通常一个人去看剧。一个人时有更多时间观察他人。我见过带着4、5岁的孩子,要他不看字幕听懂英文版《音乐之声》的妈妈、还见过为了彰显自己的专业而跟着演出一起高声歌唱的中学生;见过像磕了药一样随着音乐夸张扭摆的年轻男人、还见过外表斯文却全程骂老婆的伪君子……年底去看《卡门·古巴》的时候,身后有两个女孩子一直在小声讨论,于我而言无妨,但恼怒了坐在我隔壁的女孩子。隔壁的女孩子一回头说了句语气很冲的话,嫌她们吵。我当时非常害怕,我害怕她们一来一回争论不休吵个没完没了,这是我司空见惯的场景,我真的很害怕在剧院这样的场合遇到,所幸身后的女孩子们没有听到。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拥有人文艺术气息的环境里,人还是可以像带着引线的火药桶一样,一触即发,难以安静……出入高雅的艺术场所好像能让人瞬间变得有气质、有涵养,但于有些人而言也只不过是披着件文艺的外衣,毕竟不落俗是最俗气的梦想。
为了了解音乐剧,我加过几个音乐剧群组,但基本也只是为了获取一些资源,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人。群组里的人热情,但又大量地用着一些昵称、简称,这让当初初识音乐剧的我很是苦恼。他们聊起那些音乐剧演员的时候,像是在聊一个认识很多年,非常熟稔的老朋友,可以说出很多他们的趣事。可惜我对这些老外实在无感,无法像对待一个偶像一样,永远对他们保持热情。
凡是我觉得好的东西,我愿意一次又一次地推销给身边的朋友。也许有一天,他们闲来无事点开了我的分享链接,就会像我一样,深深地被音乐剧吸引力。明年又有很多好剧来上海了,有机会,去剧院看看吧。
音乐剧作为一种现代的舞台综合艺术形式,以美国百老汇为首风靡世界。随着音乐剧文化的输出与交流,自20世纪70年代起,音乐剧不再局限于美国,而是拥有了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德奥、法国、日韩等多个创作中心。作为小语种音乐剧的代表,法语音乐剧深受法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滋养,却又突破了传统的限制,在英语主导的世界中崭露出制作和审美上的独特性与开创性。21世纪以来,法语音乐剧开创性地采取先录制并发行唱片,再根据市场反响调整公演的运作模式,大量启用高颜值明星歌手,宣传与包装也开始走流行音乐的路数。在《摇滚莫扎特》首演前,主办方提前发行了音乐剧歌曲专辑,专辑在法国音乐专辑榜蝉联 20 周,2009 年经典曲目 《纹我 ( Tatoue-moi) 》连续五周在法国 SNEP 单曲排行榜位居第一,是当年法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第一名。另外一首热门单曲 《杀戮交响曲 ( L’assasymphonie) 》也当选 2009 年度最佳法语歌曲。
这种“唱片先导”的全新音乐营销方式,划清了音乐剧与传统戏剧之间的界限,也打通了法语音乐剧从小剧院走向大世界的道路。可以说,相比于端坐在严肃正式的剧场,看一部法语音乐剧更像参加音乐节或演唱会。这种种特质在需求端反映为:相较于百老汇受众,法语音乐剧观众平均年龄小、女性占比大,对于剧目有着强烈的现场渴望。
运营模式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这正是音乐剧的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相互反哺的理想结果。一部音乐剧最终想要形成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依靠的还是音乐剧本身精良的制作和演员出神入化的表演。法语音乐剧果断放弃模仿大获成功的百老汇音乐剧模式,拒绝简单的歌舞娱乐。它选择了逆溯,从遍布荣耀与创伤的历史中获取创作灵感。庆幸的是,它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2009年首演的《摇滚莫扎特》已代表了这种运作模式的成熟。
在《摇滚莫扎特》中,音乐创作者使用了多首莫扎特的原创曲调来演绎这位天才音乐家的一生,将莫扎特内心的百转千回一点点地披露给观众。在现代的编曲和古典的旋律中,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
在坠入爱河的莫扎特收到父亲的信时,那首《谴责父辈》(J’accuse mon père)以摇滚电音发泄出父亲对莫扎特沉湎欢愉的失望与指责,“小丑”角色的出场也反应出莫扎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这首歌曲被观众戏称为“吼叫信”,它不仅再次将观众的情绪带向高潮,也自然引出了剧情的反转与过渡。
▲《摇滚莫扎特》中的《谴责父辈》(J’accuse mon père)剧照/图源:豆瓣
不仅如此,法国音乐剧“写意与浪漫”的独特风格在《摇滚莫扎特》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近乎夸张的符号化装扮,放大了莫扎特身上的浪漫气质与自由天性;歌词中“打破镀金牢笼”的诗意化表达,隐晦而耐人寻味。
另外,《摇滚莫扎特》在舞台细节上的把握也十分精准。莫扎特身处的18世纪,正是洛可可艺术引领风骚的鼎盛时代。细看剧中人物装扮,不论男女,都佩戴着纹有18 世纪经典花边的领结。灯笼袖和夸张的裙撑,也是洛可可风格的标配。在主角进行单曲演绎时,舞台的其他地方也会同时上演一些小故事,使观众目不暇接。
正因《摇滚莫扎特》几乎汇聚了现代法语音乐剧的所有特质与精髓,它才能够享有空前的声誉。如此将经典的文本与流行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是法语音乐剧铭记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也是对流行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开拓。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