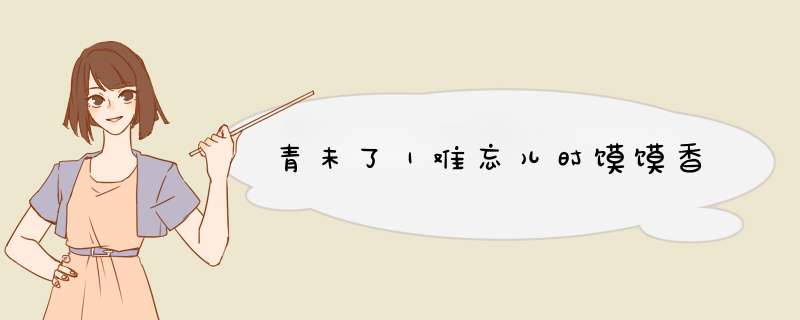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们正准备吃晚饭,父亲接到一个电话,是本家一个叫“建华”的晚辈打来的,邀请父亲提前回滨州老家,与其他长辈一起商议他女儿出嫁的相关事宜。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具体谁去送闺女、谁去送嫁妆、谁去跟轿、谁去做客等等细节都要研究一下才好。
我随口问父亲,现在咱老家招待亲戚还得去馍馍房换馍馍吗?父亲说,现在都去饭店开席了,面食要啥有啥,村里的馍馍房早已风光不再了。听罢此言,我怅然若失。
“民以食为天”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则是人们风趣的共识,而我们的先祖更是依靠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广袤平原上的辛勤劳作得以繁衍生息,小麦、玉米是这里一年两季最常见的粮食作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尽管加工后的玉米面可以用来蒸窝窝头、糊饼子,但玉米面毕竟是粗粮,不易消化,不可以天天食用。纵然白白的米饭在今日也不再是富贵人家的专利,家家都可以吃得起,但粗硬的米粒,作为鲁北地区的老年人吃不了,年轻人吃多了胃里也会发酸、发胀。于是,馒头以它松软可口、老少皆宜的特性,成为了北方一日三餐最常见的主食,受到北方人世世代代的钟爱。
在里则老家一带,不管是圆圆的馒头还是长方形的“切卷子”,人们都习惯称之为“馍馍”,也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更简单称之为“干粮”,去馒头房买馍馍或者用麦子换馍馍的行为统统称之为“去拿馍馍的”或“去拿干粮的”。离乡多年的我,现在一想起来这些浓浓的乡间俚语,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是八零后,虽没有忍饥挨饿的经历,但打小吃的却是自己家磨面蒸的“红馍馍”。也许是面粉里面含有麸皮的缘故,刚蒸出的馍馍还是白色的,可连续馏上几次之后就成了红色的了。特别是用大铁锅做饭,柴火烧得又旺,锅也热得快,馍馍不久就会发干、开花爆皮,吃到嘴里干干的、硬硬的。许多牙口不好的人,吃饭时就会把干馍馍皮先扒下来,泡到稀饭里,泡软了再吃。也有日子过得比较殷实的人家,会把扒下来的馍馍皮收起来,饭后再用来喂鸡、喂狗,但这毕竟是少数。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村里或镇上的馒头房用精粉做出的白馒头相对而言就是“大家闺秀”“高富美”了,不仅对我们贪吃的小孩子是一种诱惑,也成为了招待亲朋好友的必选之物。虽然一斤二两麦子才能换一斤馍馍,但明事理的乡亲们在重要接待当口也不含糊。娶媳妇嫁闺女,盖屋打墙,总要用好的酒菜、白白的煊和(huo)馒头慰劳前来帮忙的乡亲、好友。把好东西与大家分享不仅仅是为了面子,也是乡亲们淳朴厚道的真实体现。
我是家里的长孙,当时小姑还在上学,父亲和母亲常年上坡里侍弄庄稼,所以每当亲戚们家有新婚嫁娶、添丁进口的喜事需要走动时,奶奶总要带着我一起去坐大席。那时候,附近的村里喜欢用一种长长的白馍馍(后来知道叫“签子馒头”)招待坐席的亲戚。这种签子馒头是馒头房专门做出来的,开席前,主人家根据坐席的人数和落忙的人多少去预定。白白的热馒头放在一个圆形的大簸箩里,用多层白色棉被盖好抬回家,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陪客的人大呼“上饭“”时,帮忙的小伙们快速把它端上桌,不冷不热刚刚好吃。陪席的人,热情地说着喜庆的话,把签子馒头一个个地递给远道而来的亲戚们。那些饭量大的男客,因光顾着喝酒,菜吃得少,所以能吃下一斤馒头;奶奶她们这些女客不喝酒,吃菜就多一些,馒头自然吃得不多,往往是把一个长馒头从中掰开,相邻的两人一人一半。
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我们这些小孩子,来坐席的路上还念念叨叨“跟着大人去坐席,吃丸子肉喽”!可是一坐到饭桌前根本就不知道啥是好菜了,上来啥就抢着吃啥,哪怕是开席前放在小碟子里的蜜枣、小点心、蜜三刀也被我们快速吞下了肚子。加上吃席时大人们不断地给我夹菜,在还没上硬菜“肘子”前,小肚子早已鼓鼓的了,我们实在是吃不下了。
陪席的婶子大娘们常年忙于此事、经验丰富,早已熟门熟路,十分周全,陪不好客人还行?只见一个大娘脸上笑成了花,从一个热乎乎的长长馍馍上掰了个馍馍尖递给我,看着我的眼睛说:“好孩子,来,吃个馍馍尖,长大好做官。”见此情景,奶奶只好说:“你大妈疼你,快接过来吃了吧。”我只好遵命,默默地把馍馍尖接过来吃了下去。
后来家里有了小妹,奶奶和我们分了家。因为家里有十来亩地,父亲也无法外出打工,没有钱花的时候只能卖粮食,一切收支只能“地里进地里出”,家境每况愈下。每当夏、秋两季遇到淫雨霏霏、不见晴日的连阴天,看到火屋里储存的干柴越来越少,父母为了节约烧柴(有电炉子不舍地用),就把一天三顿饭改为两顿。早晨做饭时多放上几个馒头,吃完饭后继续把热馒头盖在锅里,谁饿了谁去拿,不再一起吃饭。黑天前,父母会安排我去馒头房拿刚出锅的热馒头回家直接吃,怎么省事怎么办。
每次都是我拿着写有壹斤、貮斤、叁斤不等的馒头票,沿着胡同里的小路去村子南头的馒头房“抢”馒头。说是“抢”,一点也不为过。附近好几个村子,数这个馒头房大,而且干净、卫生。馒头房中午、下午黑天前各蒸一次,一次蒸七八屉,也许是怕蒸多了剩下不好卖,每次出锅的热馒头多少斤都有数,一会就卖光了。很多人怕抢不到热馒头,于是提前十几分钟来等着。我不怕,因为我与他家的大女儿同学,两家的地又挨着,早就混熟了。每次我进去后先叫婶子,再拿起袋子自己装馒头(一斤几个我已经记在心里了),不用像别人一样排队等着主人给装。过完称,交上票,我拿着个热馒头边走边吃。馒头咬起来软而有劲,嚼起来满嘴浓浓的麦香,越嚼越甜。有时我甚至怀疑面团里面是不是放了糖,后来长大上了学才知道缘由。
有时在路上忙着玩,不小心把馒头掉在了地上,也不嫌脏,扒扒皮接着再吃。我相信,每一个乡下的孩子对《悯农》这首诗都不陌生,见惯了父母的辛劳,也就更懂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了。
记忆中,父亲每几个月都会用化肥袋子背着一大块麦子去馍馍房换成馒头票。有时家里来了亲戚,或者自己蒸的馒头不够吃一顿了,或者农忙时间没有时间自己蒸馒头的时候,就让我去拿几斤接济一下。有一年,父亲在邻村干建筑时听说杜店镇张官村有个馒头房做的“切卷子”馍馍很筋道,年底下就和几位邻居骑着自行车驮着半袋麦子去换了一些馒头回来。那些馒头确实好吃,用压面机压得一层层的,很有嚼头,以至于让我感觉到这个春节都与众不同。后来上了学,参加了工作,吃过了各种各样的白馒头。也许是吃久了吃厌了,反而想念起母亲蒸的“红馒头”了。我们结婚后每次回家都要带几个母亲自己蒸的馒头回来,吃着面皮有些发黄的馒头,就好像母亲在身边一样。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结婚有了小孩后,母亲便来邹平照看孩子。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母亲说总这样买着吃太贵了,五块钱的馍馍还吃不到一天,我去买个带多层蒸笼的电锅,你去买一袋面粉、一块鲜酵母,咱自己蒸来吃吧。面团发好了,为了好揉面,母亲又抓了一把玉米面进去。望着一大盖垫准备上锅的馒头,我和妻子都有着别样的感觉,感受到了家的温馨,感受到了由老人关怀带来的幸福感,联想到了母亲多年来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心中五味杂陈。半小时后馒头出锅了,母亲把锅盖揭开跑跑热气后,左手端了半碗凉水右手一边沾点水,一边快速地把热腾腾的馒头拿出来晾在浅子里。我忍不住赶紧拿了一个,咬一口软软的又不失筋道,就着大葱蘸酱,大快朵颐,好像找回了儿时的感觉。从那以后,我家时常自己蒸馒头吃,蒸馒头的人有时是母亲,有时是妻子。不变的是,馒头里那麦香的味道、家的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岳母因为吃不惯市面上的精粉馒头,多年来都是自己蒸馒头吃。前年国庆节去我老家做客时,吃到了父亲从馒头房拿回的签子馒头,赞不绝口。母亲见状非常欢喜,又去馒头房拿了十斤,嘱咐我给岳母家五斤,带回我家五斤。打那以后,父亲每次来邹平,都要带几斤签子馒头来,说是用自家的麦子换的,不花钱(不用花我们小两口的钱),同时也为了省事,省得我们经常蒸馒头太累。
这次来邹平,除了馒头,父亲还带来了五斤挂面。父亲说,这些馍馍和挂面都是从村西头你表舅家换来的,他们靠着“换馍馍”、“换挂面”,用十年的时间不仅盖起了一座小楼,还供出了一个大学生。别看二两麦子不起眼,小账就怕大算,全村的人都来拿他的馍馍,一年下来就不是小数目了。父亲说,靠汗水和勤劳发家致富,总是令人羡慕的。
听着父亲的话,望着厨房里正在忙碌的母亲和四周飘散的缕缕热气,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句民间耳熟能详的歇后语“人活着就是为了不蒸馒头——争口气”。人就应该争一口气的,不管是为了父母孩子,还是为了自己,不是吗?
(本文首发于“滨州文学”,后被多家刊物转载)
作者简介:王冬良,企业员工,爱好写作,偶有文章发表。系省散文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获大平原文学创作奖。
壹点号 糖业清风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