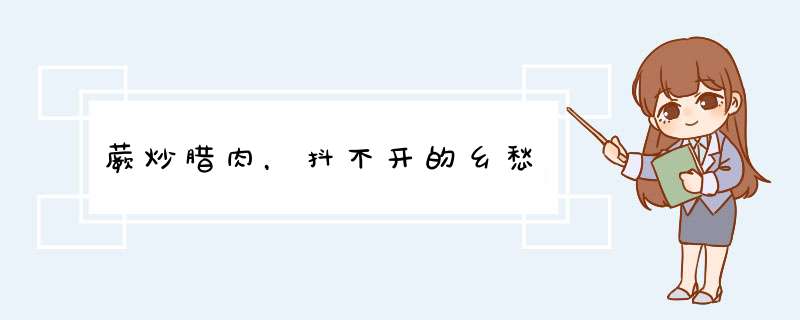
在城里,总免不了跟亲友餐聚、小酌,席间有人问我,你最想吃什么,我脱口而出: 家乡的蕨炒腊肉。
谈起家乡的蕨炒腊肉,也令同乡都忍不住馋涎欲滴了,一股浓浓的乡愁充溢在心里头。
我老家地处巍峨的相思山麓,相传是当年刘邦追张良的地方。那儿没有大湖大江,也没有岳阳这么多高楼大厦,但有山,四周都是,山上资源特丰富,盛产竹木,尤其是一种叫蕨类的植物,普山普岭俯拾即是。每年三四月,由于春风春雨的滋润,蕨就得意地生出鹅黄色的嫩芽,滋滋地往上窜,一个晚上能长一两寸。
晴空万里,是采蕨的好天气。村子里的大姑大嫂们,争相上山,拨开密匝匝的荊棘,蹲在绿得发亮的蕨类植物跟前,细心地采摘,没半天工夫,竹篮里堆了尖。有人采摘蕨时,总是喜欢用小铲连蕨菜的根一并铲了去。断了根,蕨菜就少了,蕨菜似乎挥着“拳头”向她们抗议过,然而无声的抗议总是那么的无助。
拎了盛满蕨菜的篮子,蹬着嘉陵去镇上,将蕨菜摆在街道两边,希望卖个好价钱,便扯起喉咙,把一声声的叫卖,喊成一串串紫金铃。卖主拿回家,将鲜蕨淖一下水,切碎,爆炒,别具风味。
当然,大多数人会将采摘的蕨菜,洗净,晾晒干透,贮存,准备年头岁尾,来个蕨炒腊肉,那才叫山珍海味。
据《本草纲目》载: 蕨,性平,味甘,可食,能坚骨补肾、活血止痛;治湿热黄疸、水肿、吐血;茎可治虫积腹痛、流感等症,亦用作除虫农药;乌蕨在民间作治疮毒,及毒蛇咬伤药等。
早在我国周朝初年,就有伯夷、叔齐二人采蕨于首阳山(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下,以蕨为食的记载,可见我国劳动人民早已开始食用蕨类了。被人们食用的种类有菜蕨、紫萁以及莲座蕨目的大部分种类。我老家食用的是菜蕨。
不过,蕨炒腊肉史上没有记载,也无从考证,恐怕这是山区一大发明吧。吃,自然是生存的第一要素,可爱的老家人厚实丶聪明,就在把吃发挥到了极至,先前是干笋炒腊肉、干豆豇炒腊肉、干萝卜炒腊肉,后来又发明了蕨炒腊肉,后者比前者高了一个档次,成为一道山里人特爱吃的美味,让人回味悠长。
年关将近,你到山区去看看,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挂满了被柴火熏得深黄的腊肉,灶台上搁着一把把用稻草扎紧的干蕨。显示出农家一份富足、恬静与祥和。
客人一进门,主妇就忙开了,张罗着做道蕨炒腊肉,这几乎成了农家待客的不变仪式。先将干蕨切成小块,倒入烧红的锅里炒几转,加入蕨和盐、生姜、新鲜辣椒来煽炒,盛入盘中。腊肉,原本油腻,拌上筋道的干蕨,去了油,不腻,使咸香柔软的腊肉,愈发衬出蕨菜特立独行的韵味。
蕨炒腊肉,吃的是野菜,奔的是那份从大山深处飘来的淸纯,吃得你“呼啦呼啦”摇头晃脑,直喊“透鲜”、“透鲜的”,饮上三杯老谷酒,浑身鲜抖抖,萌萌哒,打个饱嗝,伸伸懒腰,那才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和蕨炒腊肉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是上在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我刚当“孩子王”。农忙时节,我被安排到山旮旯里的小山村“支农”,住在李大娘家里。从早到晚,挑粪、整田、插秧,累得骨头都像散了架。吃的是米拌茴丝粥、没油星子的“红锅菜”,一个月下来,一个壮实小伙子整整瘦了一圈。
一天中午,粗瓷碗里盛着干蕨炒腊肉,一股香气弥漫开来,眼角尽是欢喜。我馋极了,还没下著,一旁的小孩提前向碗里发起了进攻,大娘就搧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哇哇地哭起来,大娘斥道,老师累瘦了,这菜是给他补身子的。眼角尽是欢喜。
后来才知道,干蕨是家里贮藏的,腊肉则是她用半袋茴丝去邻居家换的。天啦!半袋茴丝可是一家人七天的口粮呢。我心里一热,泪水哗哗,翻江倒海。
蕨炒腊肉,包含了太多的人生沧桑,我永远永远记住了你这普通不过的名字!
不久前,我收到一包鼓鼓囊囊的蕨菜,是老家亲戚捎来的。褐黄色,一根一根如蚯蚓,紧紧粘在一起,有淡淡的香味窜出来,十分好闻,引起邻居的羡慕。
沧海桑田。社会发展到今天,大鱼大肉吃多了,吃腻了,就想換換口味,尝尝农家味道。和藜蒿丶地米菜等诸多野菜一样,蕨菜也成为文人骚客讴歌的题材,倍爱食客们的青睐,让“沉寂”多年的蕨炒腊肉,堂而皇之搬上了餐桌。据说,蕨炒腊肉以“脆嫩爽口醇香柔润”的特点,被定为“品牌菜”,还被搬上湖南都市屏幕,这一消息着实让许多山区人“爽”了一把。
在城里宴席上,这道“品牌菜”尽管油盐很足,佐料也很足,可总是吃不出少时的那种味道了。因为每次吃它的时候,我就想起陈大娘,好像陈大娘就坐在我的对面,默默地注视着我。浓浓的乡愁、乡情在心底升腾,升腾......
来源:岳阳日报特稿部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