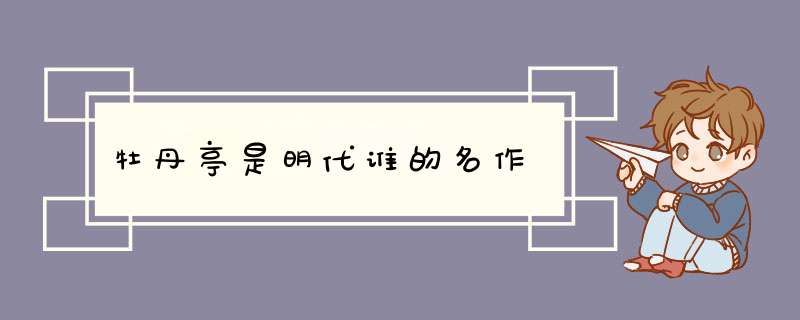
牡丹亭是明朝汤显祖的作品。文中描写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体现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生活的追求。而且《牡丹亭》是明代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最得意之作,他曾言“吾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
说起汤显祖,就会想起《牡丹亭》。但奇怪的是,一说起《牡丹亭》,人们能够想起的大概就只有《闺塾》、《惊梦》、《寻梦》这几出(全剧五十五出)。
不止此,有些重要关目还令人扫兴。当杜丽娘回生之后柳梦梅要跟她“今宵成配偶”时,她却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鬼可虚情,人须实礼”而严颜拒绝。由于五四以来的观众把杜丽娘的“惊梦”当成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争取恋爱自由的爱情剧,因而这“人须实礼”的重要关目便让观众大失所望。
事实上,把《牡丹亭》视为爱情剧,是小看汤显祖;把《牡丹亭》主题理解为反抗封建婚姻制度,那又是拔高汤显祖。汤显祖所思考的,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命题:什么是真正的儒家精神?在“真儒”思想体系中,人欲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个体的自主性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这种思考从他创作八股文的少年时代便已开始。由制义而至传奇,正可看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其变化。
从八股文到《牡丹亭》以性情之道,求孔孟真心
汤显祖曾为包熺《宋儒语录钞释》作序,并评价此书“此孔、孟正脉也。”他最为追慕周敦颐(字茂叔)和程颢(字伯淳)。所谓“以为绝学梯航”者表明,在他看来,“孔孟正脉”在他那个时代已成绝学。他早年所作的八股文是他对“孔孟正脉”的理解的一份心得。
汤显祖所作制义,明清时文集多有录入。这些制义并不完全是为应试而作。明清的制义,有一定的在社会上传播的渠道。这种独立于科举考试之外的传播渠道,使八股文创作可以达到“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的地步。由此,八股文的创作进入了审美的境界,成为一种“美文”。
汤显祖在其制义中始终执着地去表达他对儒家经典的独特理解,这就涉及他所受到的王学左派的影响。他于13岁拜罗汝芳为师,对“孔孟正脉”的体认富于心学色彩。《夫妇之愚……所憾》篇,其题来自《中庸》,朱熹点明,《中庸》的这段话,强调的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但汤显祖则把朱熹所说的“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的意思加以放大,把“夫妇居室”与“百姓日用”联系起来。他说:“圣人虑善,反有借知于匹夫匹妇者。……圣人立事,反有借能于匹夫匹妇者。”
援佛入儒、三教合一,这本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共同特点。但明代有一种主流的经义学观点,认为八股文的写作应该“理醇”,不应渗入释道、子书。但在心学的影响下,罗汝芳的入室弟子杨起元却做起了援佛入时文的实验,以二氏入制义很快就形成为一种风气。
汤显祖的制义借助于二氏,一方面强化了心学体验的表达,另一方面则令词华多变绚烂。汤显祖的援二氏入八股文,有一些是借二氏术语诠解儒家经义,如《诗云缗蛮》一文,基本上是在演绎四书经义与朱熹的传注,流露出的是一种援佛入儒的旨趣。有一些则是试图通过援二氏入儒以表达新的见解。如对于出自《大学》的《身有所忿》一题,此一题目到了汤显祖手里,便引入了老子《道德经》和佛教理论,由“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到“以太虚为宗”、“以终灭为验”,多方设喻,令人眼花缭乱。汤显祖充分利用八股之排比,每引入道家或释氏,便有相应的术语排偶而出。他之追求机变、微眇、奇异,目的是为了表现富于个性的心灵。
不惮狂狷追寻“孔孟正脉”
汤显祖的八股文代表着隆万时期的新变。对于这一时期的新变,当时及后世的卫道者纷纷表示担忧乃至愤恨。作为明代八股文的总结性人物,崇祯间艾南英感叹“隆万而降杂以俚矣”(《今文定序篇下》),“制举之业至今日败坏极矣”(《戊辰房书删定序》),而隆万则是天、崇间“败坏极矣”的八股文风的源头。
万历十五年(即汤显祖中进士的四年后),礼部尚书沈鲤在其上疏中说,当时的八股文写作越来越远离儒家经典,沈鲤向皇帝提议:今后“如复有前项险僻奇怪决裂绳尺,及于经义之中引用《庄》、《列》、《释》、《老》等书句语者,即使文采可观,亦不得甄录,且摘其甚者,痛加惩抑,以示法程。”(《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四)援二氏入儒被视为文章之流弊。
隆万八股文风实是王学影响的直接结果。这一点,艾南英看得最为清楚。他说嘉靖、隆庆以前,士子谨守程朱的传注,但“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此后浸淫无所底止。”(艾南英《历科四书程墨选序》)“华亭”指嘉靖末首辅徐阶,“兴化”指隆庆间首辅李春芳。
徐阶推崇阳明学,有姚江弟子之称。李春芳曾是阳明后学王艮的学生,于隆庆二年继徐阶为首辅。这两位王门弟子相继为首辅,再加上徐阶的讲学活动,阳明学不仅在官学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而且经由科举这个平台向整个举业辐射。所以在制义中援引二氏、百家杂说,这是儒学在晚明发展、变异的一种形态。汤显祖八股文创作正是徐、李二首辅“执政尊王氏学”时期,他的追寻“孔孟正脉”汇入了这股时代思潮之中。
汤显祖对真儒的追寻并非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也不是虚玄的冥想,而是与具体的政治实践、道德实践息息相关。就在他中举之后尚未进入官场的时候,张居正欲其子及第,拟罗致海内名士以撑门面,看中了汤显祖。这种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愿”作派冒犯了汤显祖的价值信仰,他拒绝了张居正的延致。
现实政治中的极权主义(以张居正、申时行为代表)手中不仅拥有行政极权,而且拥有意识形态上的极权。天理成了他们强化个人极权、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这一类人才是孔孟儒家的真正的异端,是李贽所口诛笔伐的道德伪饰者。在《攻乎异端》一文中,汤显祖说:“夫学道者将以利天下也,攻异端者则害而已矣。……然其害也,非私其情于己,则玩其志于时。无益性体,只见其乱道真而长浮俗也。”
追寻“孔孟正脉”,这既是对孔孟儒家与宋明理学的比较的结果。也是对于现实政治实践深怀失望的产物。他的所谓“余意所至,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真正的含义是:坚守道德贞 *** ,不惮身为狂狷,愿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去追寻心中那个真正的孔孟正脉。
情多想少对《牡丹亭》的“忏悔”
占去了晚年主要精力的是他的传奇创作。万历二十五年,汤显祖完成了《牡丹亭》。第二年他赴京上计后即告归回临川,写了《牡丹亭》的题词,并刊行该剧。在此前后,汤显祖与达观和尚有过一些关于“性”与“情”的讨论。这些讨论是《牡丹亭》创作的重要背景。
达观在给汤显祖的信中说:“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矣。”又在后来的《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说:“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痎疟,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非类。”
这篇文章常被理解为汤显祖晚年对于“情”、对于《牡丹亭》的忏悔录。事实上是他依然执着于“情”的无奈。“情多想少”固然使他历尽人生磨难,但他清醒意识到“出世之难”的千古同慨。
《牡丹亭》是在“情”与“性”(而不是“礼”)的相对待中展开艺术思维的。杜丽娘因《关雎》而兴二八之叹,因游园而感生命之萌发、情欲之骚动、之升华、之对象化,因青春与美丽之付与断井颓垣而痛苦,因而寻梦、写真、一病而亡。
这种艺术呈现表明:情欲是天生的、自然萌发的、美丽迷人的,因而它是合理的。至于此剧后半部分的寻求杜丽娘父母的认同,则又表明情欲与礼法是应该合一的。究竟是为了存天理而必须灭人欲,还是仁、礼统一,把礼法建立在人的感性需求的基础上?
从早年的八股文创作到晚年的《牡丹亭》,汤显祖一直在用独特的方式思考着儒家的真义。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