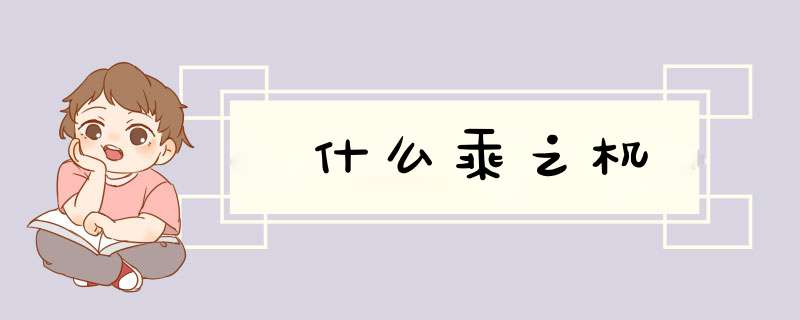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王朝历经三代帝王花费八年时间才宣告平定。
但是由此引发的藩镇割据一直困扰中晚唐的政局,甚至也深深影响了此后五代十国的乱世以及北宋高度抑制武官的政治体制。
为什么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没有彻底解决藩镇问题,为什么中晚唐多位皇帝认识到“藩镇割据”的危害却无力根治呢?安史之乱是一场妥协的胜利安史之乱由安禄山在公元755年发动到公元763年,唐代宗时期宣告平定,历时八年,期间唐王朝有过多次提前结束叛乱的机会,但是都被唐玄宗和唐肃宗父子错失,导致最终唐王朝耗尽国力,无法取得完胜,最终唐代宗只能用“妥协”的胜利方式来结束这场叛乱。
公元761年,安史叛军的第三任领袖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弑杀。
这一事件标志着安史之乱开始走向终结,此前唐王朝与安史叛军之间在战场上还互有胜负,甚至安史叛军还气势更盛。
但是史朝义弑父自立后,安史叛军内部开始离心离德,逐步走向衰亡。
公元762年10月,唐军收复洛阳,史朝义狼狈逃往老巢范阳。
而此时安史叛军中的大将开始纷纷投降唐朝政府,安史之乱在这些将领的叛乱中以极快的速度结束。
公元763年春,田承嗣投降开始,李怀仙、李宝臣、薛嵩等人相继投降,众叛亲离的史朝义自杀身亡。
收复洛阳后不到半年,安史之乱宣告平定。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安史之乱是在安史叛军实力尚存却纷纷投降的情况下得以平定的。
唐王朝对安史叛军没有进行过摧毁性的打击。
被安史之乱拖得精疲力竭的唐王朝不断的接受安史叛军的投降,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安史之乱的结束是一场妥协的胜利。
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史之乱的平定是消灭了叛乱的首领,没有消灭叛乱的根基或者没有消灭叛军的主体。
叛乱是在没有任何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这种方式反映在763年河北建立的新权力结构方面。
朝廷不但愿意赦罪和保证安全,而且确保叛乱将领的权力和官阶,其原因有二:它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急于结束敌对行动;它预料一旦和平和现状得以确立,就能够控制以前的叛乱将领。
但在这时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就不如预料的那样。
河北——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富饶的道之一——这时一分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为节度使的前叛乱将领手中。
政府与其说是镇压叛乱,倒不如说通过妥协的解决办法来结束叛乱。
在河北,妥协的代价证明是昂贵的。
《剑桥中国隋唐史》妥协胜利的高昂代价安史之乱以这种妥协的方式平定,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有着极其高昂的代价。
“河北三镇”犹如独立王国,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央,而参与平叛的主力军队都仿佛从这次叛乱中得到启发,渐渐也有尾大不掉之势。
而连续错失机会的唐王朝却极度虚落,没有皇帝直属的常备中央军,或者没有皇帝直属的有战斗力的军队。
因而只能无奈的采用这种妥协的方式来结束叛乱。
妥协使得唐王朝权威下降:唐王朝作为中央政府对全国尤其各军镇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安史之乱中只有发动叛乱的领袖被惩处,作为叛军骨干的田承畴、李怀仙等人却不仅免于处罚,而且保留的军权和官阶,更可笑的是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地盘,摇身一变纷纷出任一方节度。
这些叛军骨干极其部下的结局让唐王朝的中央权威急剧下降,掌握军队的骄兵悍将已经不把唐王朝放在眼中,他们只是名义上服从而已。
“河北三镇”带来极坏示范作用:河北三镇是安史叛军的三位降将受封的三个军镇,他们分别是魏博节度使田承畴;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
这三人控制着当时唐王朝最富庶的河北地区,也就是安史叛军的老巢。
作为降将他们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自己署置将吏官员,各握强兵数万,租赋不上供,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他们成为后来困扰唐王朝的“藩镇割据”的最主要代表,后来的唐朝皇帝试图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大都针对“河北三镇”。
由于唐朝政府的权威下降,加上“河北三镇”的负面影响。
中晚唐时期唐朝主要军事支柱各地军镇都有了这种“离心倾向”。
这里倒不是说所有军镇都不服从中央,但是这些掌握军队的藩镇与唐朝政府之间的关系的确变的非常微妙。
唐朝政府不信任带兵的武将,而这些骄兵悍将也反过来经常与唐朝政府搞点“摩擦”。
安史之乱中为平叛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的叛乱,李光弼的避祸不朝,以及德宗时期的“泾源兵变”等等都是这种离心倾向带来的恶果。
唐朝政府与“藩镇”的斗争自唐代宗之后,唐朝政府也不止一次着手解决藩镇割据问题。
虽然也有一些时期取的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唐宪宗时期连最桀骜不驯的河北三镇都归降中央,接受唐朝政府的人事安排。
但是这样的情况仅仅是中晚唐为数不多的几个时期,大体上这些藩镇都是利益不受损害时接受中央管理,一旦触犯切身利益就断然翻脸。
特别是“河北三镇”在宪宗死后很快又恢复到“独立王国”的状态。
唐代宗之子唐德宗是中晚唐第一个开始向藩镇发起挑战的皇帝。
但是很快他就被自己派往镇压藩镇的军队反叛,酿成“泾源兵变”。
此后唐德宗一改对藩镇的强硬态度,恢复到姑息状态。
唐德宗之后的唐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之后继位的唐宪宗是中晚唐对藩镇问题解决的最好的皇帝。
他上台后先后平定了四川节使度刘辟、镇海节度使李琦,招降了河北三镇,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并且使藩镇相继降服。
唐宪宗在位后期宠信宦官,使本已存在的宦官专权现象在之后急剧恶化。
他死后继位的唐穆宗贪图玩乐,使唐宪宗在削弱藩镇割据问题上取得的成果重新丧失。
后来的唐敬宗和唐穆宗一个德行,藩镇割据问题没有好转,宦官专权倒是日趋严重。
此后继位的唐文宗试图振作革新,结果因为甘露事变直接成为宦官的傀儡。
所幸之后的唐武宗和唐宣宗重新振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和藩镇的力量,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乘吐蕃和回鹘的衰落,收复了部分因安史之乱失去的国土。
唐宣宗之后的唐朝皇帝大都昏庸无能,唐王朝也在这几位皇帝手中彻底走向衰亡。
最终被藩镇割据的另一个版本,即黄巢起义的降将和镇压黄巢起义崛起的新藩镇军阀朱温等人彻底摧毁。
综上,唐朝政府不是没有为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进行过努力,但是都因为宦官、党争等等因素掣肘,导致功亏一篑,最终被新的藩镇军阀推翻。
某种意义上来说,唐王朝是无兵、无钱、无力根治这些顽疾。
中晚唐的三大顽疾使唐王朝无力回天“藩镇、宦官、党争”是困扰中晚唐的三大顽疾。
藩镇的危害并非没有人认识到,中晚唐有多位皇帝都立志要解决这个痼疾。
但是安史之乱后的其他两个问题开始出现并严重影响了唐朝政府的正常运转。
使得唐朝始终无法全力解决“藩镇割据”这一问题。
宦官专权:这是中晚唐困扰唐王朝的另一大顽疾,甚至在后来的危害性远远大于藩镇割据。
但是这一问题的抬头实质上也是由于安史之乱以及由此引发的藩镇割据。
在安史之乱中,唐肃宗灵武即位,组建新政府平定叛乱。
他身边的宦官李辅国出力甚多,因此也在肃宗时期权势惊人,到了唐代宗时期甚至让身为皇帝的唐代宗都不得不叫他尚父。
此后另一位宦官鱼朝恩更是控制了西北强军神策军,并使这支军队成为了唐朝皇帝的禁卫军,从此皇帝身边的宦官彻底掌握了这支禁卫军的军权。
宦官通过掌握军权,在后来甚至可以废杀皇帝,中晚唐很多时期都是宦官掌握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力。
“党争”:虽然唐朝的党争最著名的是持续40年左右的“牛李党争”。
但是由此带来的唐朝政府内官员的互相攻讦,结党斗争,给唐朝政府的统治带来极坏的影响。
到了后期这些党争又依附与宦官,百官平日按宦官的政令推行政务,又依附不同宦官相互攻击夺权,导致后期唐王朝的政局日益混乱腐败。
伴随着藩镇割据问题的产生,宦官专权和党争两个问题也开始困扰唐朝政府,这使得唐朝政府内外交困,对外没有强兵遏制藩镇,对内宦官专权和党争又使得政局混乱,唐王朝即使有心解决藩镇割据,也陷入有心无力的困难境地。
“安史之乱”是中华民族的浩劫,唐王朝历经三代帝王,花费了长达八年时间才“宣告平定”,注意我用“平定”,没有说胜利;而随后“藩镇割据”灾难又接踵而来,一直伴随着中、晚唐政权的一百多年。
为什么唐王朝没有治理各地的“藩镇割据”呢?安史之乱由公元755年唐玄宗时期开始,到公元763年唐代宗时期宣告平定,延续八年,期间李唐王室有多次完胜的机会,但是由于唐中央政策失误而延期,直打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国力凋敝,万般无奈,唐代宗才以“让步的胜利”方式,结束平叛!安史之乱结束时,叛军实力没得到剿灭,只是有条件地暂时“投降”,没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各路军阀都迫于形式“貌恭而心不服”,平叛“胜利”之日已经为“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这种近乎荒唐的、“妥协”的方式平定,留下了巨大后患,河朔范阳、成德、魏博三镇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央,实际上早形成了“独立王国”,而各路参与平叛,并有成效的军队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于唐王朝此时财政困乏,中央无精锐武装力量,纵使地方军阀暗中与中央政府“掰手腕”,唐中央只能假装包容。
由于安史之乱的教训,李唐王室不再信任边疆带兵的武将,而这些自恃平叛有功的将领,也经常给唐朝政府增加点“麻烦”,怪现象纷至沓来:平叛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突然发生叛乱,能征惯战的李光弼为避祸不上朝廷议事,以及后来的“泾源兵变”等等都说明唐中央政府已失去了对各个军阀的掌控!其实,李唐王室曾经着重解决过“藩镇割据”问题,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见过成效,唐宪宗时,不可一世的“河北三镇”的骄兵悍将都曾归降过唐中央,但这样的现象在整个中晚唐时期属于昙花一现,而且一旦藩镇利益受损害,各军阀就决然翻脸。
雪上加霜的是,伴随着藩镇割据的,还有宦官专权和党争的出现,这三大痼疾严重削弱了唐中央的权力,所以,一直到唐朝灭亡,唐中央政府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藩镇割据”问题。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