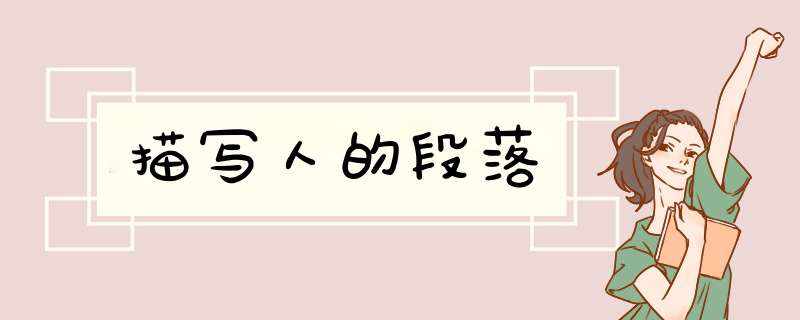
由远及近:
看见冰场上的人,穿梭一般地滑来滑去,我的心激荡着,也急忙换上冰鞋,上场去了。开始的几步,多少有些荒疏了的感觉,转了几下之后,恢复常态了。我又向前滑行,左右转弯,猛然停止,倒退滑行……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小孩,像我当初头次进冰场一样,他趔趔趄趄,一个跟头;摇摇摆摆,一个屁股蹲儿。
(配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由近及远:
卖烤红薯的老爷爷烤的红薯是金黄色的,捧在手里感觉是软绵绵的,吃起来又香又甜。卖鸡蛋的那个胖女人身材本来就不高,又没脖子,猛一看,很像一个啤酒桶。从御碑亭到问月桥,四五百米的街道两边满是摊。有卖鸽子的,卖鸽哨的,卖鸟笼的,卖鸟食的,还有卖泥人的,卖蟋蟀的,卖蛇的。甚至有早晨没卖完也挑到这里来卖青菜的。
(配图: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职业形象:
靠近东窗,坐着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被汗水浸透了洗得发白的军衣,紧裹着他那健壮而匀称的身躯。他那白中透红的清秀的面孔,像涂了油彩似的闪闪发光。两条漆黑的、细长的眉毛,有力地向上扬,将到顶端时,才弯成形。一双像熟透了的葡萄一样又黑又大的眼睛,机灵地、警觉地扫视着充满汗味和传出鼾声的车厢。他的右手,很自然地伸到衣襟下面,汗湿的手掌,轻轻握着腰间的小手槍。
(配图:伦勃朗《夜巡》)
描写外观:
这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圆脸蛋润润的,眉很赤,细长的双眼闪动着爽直的、热乎乎的目光;老是未言先笑,语言也带着笑,像唱歌似的。她走路时把身子的重心放在足尖上,总像要蹦跳、要飞。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个纯真而欢乐的女孩子,奇怪的是她那过分素净的打扮,与她的性格很不相称,也和那些爱漂亮的缫丝姑娘迥然不同:蓝布棉袄,黑粗呢短大衣,草绿色长裤,脖子上的纱巾是白的,扎小辫的头绳是根黑毛线。
(弗美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放慢动态:
跳高竿快升到我的头顶般高了,跳高运动员只剩下六(二)班的张大明了。他不慌不忙地活动了几下身子,习惯地压了压左腿,再压了压右腿,然后d跳几下。”看,起跑了!只见他迈出轻快的步子,直冲跳高架。当他快要接近跳高竿时,突然左腿在地上猛地一蹬,两手在身旁划了两个圆圈,一眨眼,身子就腾起,凌空在横竿上;刹时间,右腿一扬,左腿一翻,轻松地越过了横竿。顿时,掌声四起……
(配图:莫奈《撑伞的女人》)
过程快进:
从那以后,我每天早起练吐气,一直吹到笛子里的热气凝成了水滴淌出来。晚上练指法,直练到指头发酸发麻。对着镜子练口型,直练到镜子上喷满了雾气,擦了再练,练了再擦。经过一段时间的基本功苦练,我终于能使吐气和指法配合起来,吹出时而嘹亮、时而低沉、时而欢快、时而悲伤的调来。我牢记伯伯练好基本功的教导,便义苦学了。调、D调、F调等吹法。
(配图:爱德华·马奈《吹笛的少年》)
心理描写:
轮到我们钉了。我迫不及待地把线浸了唾沫,捻了捻。可是我一捻,把那几个小毛头捻得又细又长,穿针得时候,穿来穿去就是穿不进去。我只好把毛头拽下来才穿进去。接着,我在线得末端打上结,由于线上有唾沫,打结得时候,老是粘住手指,好不容易才把结打好。
(配图:蒙克《尖叫》)
语言描写:
我吃着香喷喷的抓饭,不时地看表。大婶今天特别高兴。说:“姑娘,不要急!有你大叔送你回去。”我正要说什么,大叔悄悄对我说:“别推辞,她又要拿我问罪了。”大婶看大叔那模样,故意瞪着眼睛问:“说我什么坏话了?”大叔一本正经把手一摊:“我怎么会在人生日这天说她坏话呢?”大婶听了,“噗哧”一声笑了。我也笑了。
(配图:杜米埃《三个交谈的律师》)
升华感情:
我突然发觉到母亲以往平滑的额头上竟出现了水波痕一样的皱纹,一条一条映了出来,“一、二、三……”我都数得出几条了。我不喜欢皱纹,恨不得用手在她额头上用力磨一磨,将那几条岁月在妈妈额头上留下的痕迹——皱纹抹去。当妈妈锁起眉心,怔怔出神的当儿,她放下毛线,呆呆地坐着。我想,母亲是忧郁的,尤其是当爸爸一去不返的时候,她时常是这样的。她眼角的鱼尾纹都清楚可见了。这些皱纹是她勤劳、伟大的见证。
(配图:达芬奇《蒙娜丽莎》)
品德例证:
记得昨天,桑老师在给我们讲课,讲着讲着,突然咳嗽了几下,我就开始觉得桑老师感冒了,接着,桑老师又咳嗽了几下,啊,桑老师真的感冒了。三十四双眼睛盯着桑老师,可桑老师却像没事似的,又开始给我们讲课。时间过得可真慢,好容易下课了,我跑过去问:“桑老师,您是不是感冒了?”桑老师说:“有点,但没什么。”后来,为了不耽误我们的功课,她背着我们悄悄地吃药。
(配图:拉斐尔《西斯廷圣母》)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