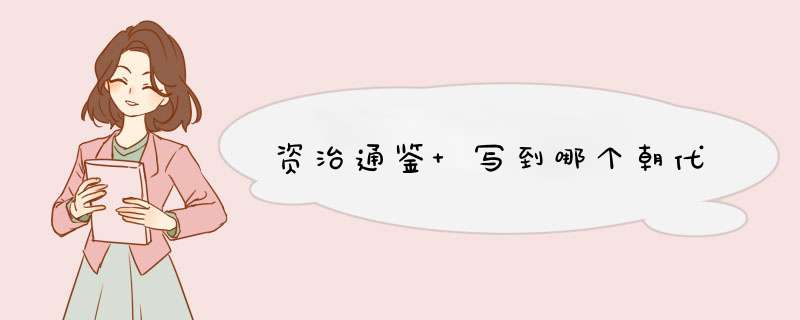
《资治通鉴》,听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部通史。
一部通史该从哪儿开始?搁一般人想,肯定得是个什么元年吧。
但这本书编年的开始,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
就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的人,听到这个年份,也会觉得很茫然吧?这一年有什么特别的?《资治通鉴》怎么会从这么不当不正的一个年份开始?因为《资治通鉴》不是史官的史书,而是政治家的史书。
▲资治通鉴全书从哪一年开始,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开宗明义之功的古代意识形态问题。
历史从哪里开始作为一部编年史,《资治通鉴》按照朝代的先后顺序,讲周朝的部分叫《周纪》,讲秦朝的部分叫《秦纪》,然后是《汉纪》、《魏纪》、《晋纪》等等,以《后周纪》结尾,因为后周以后就是宋朝,对于司马光来说就不再是古代史,而是当代史了。
每一个“纪”包含若干卷,比如《周纪》一共5卷,第一卷叫《周纪一》,第二卷叫《周纪二》,以此类推。
每一卷的开头都会标明本卷内容的起止年份。
从朝代选择上看,《资治通鉴》的内容从周朝开始,彻底抛弃了商朝、夏朝和更加久远的三皇五帝,这是为什么呢?◆从史料编纂的角度来看,周朝以前的历史渺茫难求,很难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神话,更不可能做出准确编年。
◆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儒家最为推崇的礼制,孔子想要“克己复礼”的那个“礼”,就是被周朝确立下来的,被儒家奉为圣人的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最后的那三位,也就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都是周朝的开国先贤。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你很容易推测,儒家的史书,正常会从周文王开始,或者是从周朝正式开国的那一年开始,但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偏偏选了一个不当不正的年份作为全书的开端,这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这一年,向前距离周朝开国大约6个世纪,向后距离周朝亡国182年。
◆这位周威烈王也算不上是个多么像样的天子,即便司马光对他有偏爱,至少也应该把《资治通鉴》的开头安排在周威烈王即位的元年才对,而不是即位之后的第二十三年。
◆非但《史记》那一类的纪传体史书不会这样开头,就连《春秋》和《左传》这种编年体的先驱也不会这样开头。
◆司马光为什么别出心裁,一定有他的深意。
◆要想理解这层深意,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资治通鉴》和其他史书的一种区别:并不是编年体和纪传体那种形式上的区别,而是立意上的区别。
▲资治通鉴残卷◆《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编写的史书,而不是史官编写的史书,“资治”二字是重点。
◆所以,《资治通鉴》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历史哲学专著,如果仅仅把它当成史书来读,就会惹作者伤心了。
◆作为历史哲学专著的《资治通鉴》,才一开篇就要确立一套价值体系,标榜出这套价值体系里的核心诉求。
从《左传》的结尾到《资治通鉴》的开端◆无论是一个人规划自己的职业,一家公司安排自己的运营,还是一个国家决定基本国策,都会存在核心诉求和次要诉求。
◆一个国家的核心诉求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比如强大、富裕……虽然这些诉求听上去都很诱人,但核心诉求只能有一个,其余诉求都要为核心诉求让步。
◆道理很简单:资源永远是有限的,任何一种资源调配都意味着有取有舍,对取舍的标准越明晰,运作就越高效。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由政治家 *** 刀,意图在于“资治”的编年史,一开篇就让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主角,开宗明义地讲出一个国家最应该有的核心诉求:稳定。
◆《资治通鉴》之前的一切正史,从《史记》、《汉书》到《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没做到这一点。
史官写的历史和政治家写的历史,就是如此不同。
◆借用莎士比亚的台词:在《资治通鉴》面前,“此前所著,皆为序章”。
◆从编年史的技术角度来看,《资治通鉴》是接着《春秋》和《左传》来写的。
◆《春秋》站在鲁国的角度,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开始,结束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这是孔子去世的时间。
◆《左传》作为《春秋》的补充读物,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交代了鲁哀公的人生结局,还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中原强国晋国以智襄子为主帅,进攻郑国,郑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以陈成子为主帅,出兵援救郑国。
陈成子对智襄子有一句评价,原话是“多陵人者皆不在”,意思是经常欺负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左传》有一种叙事风格,凡是这种评价性质的,带有预言意味的话,后文都会出现相应的事实,以此证明前边的评价很恰当,预言很准确。
◆既然记录了陈成子这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后文就要交代这句名言是如何应验的。
◆所以《左传》虽然编年结束在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但在全书的最后,宕开一笔,跨越多年,记载智襄子因为贪得无厌和刚愎自用的缘故,被晋国的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灭掉,这才结束全书。
◆《资治通鉴》编年的开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发生的历史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从此才有了战国七雄当中的韩、赵、魏三大强国。
◆《资治通鉴》虽然详细记载了智襄子身死族灭的前因后果,明显接上了《左传》,但从严格的编年意义上看,《左传》编年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距离《资治通鉴》开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早了足足65年;《左传》记事结束于智襄子身死族灭,这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距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也还有整整50年。
如果《资治通鉴》真想续接《左传》,为什么要留出这么大的一段编年空当呢?名分和事实,哪一个更重要?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来看,智襄子的灭族,有一场春秋战国时代罕见的大规模战役,堪比长平之战,当然值得大书特书,而周威烈王把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封为诸侯,只不过是一纸任命,波澜不惊。
再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两件事明显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前者骇人听闻,后者水到渠成。
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消灭智襄子,瓜分了智氏家族的土地、财富,“三家分晋”局面已成,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件事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然而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的意义远不如周威烈王的分封来得重要,前者只配作为后者的补充说明,不配作为一部历史哲学著作的开篇。
这样的斟酌和取舍,显示出政治家的历史观和史学家的历史观截然不同。
在政治家看来,一件表面上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事情,其实涵义重大,影响深远,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以儒家的标准来看,“三家分晋”属于礼崩乐坏的典型事件,韩、赵、魏和智氏家族这四大家族都是晋国的贵族,却完全无视晋国国君的存在,自作主张掀起内斗。
而在司马光看来,所谓“三家分晋”只是三大家族“事实上”瓜分了晋国,形成了三个独立政权,而若干年后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意味着三家作为三个新兴的独立政权,从此拥有了合法的名分,在“名义上”可以和晋国国君分庭抗礼。
也就是说,原本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竟然获得了官方认可,把自己洗白了。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名义问题是底线问题,哪怕既成事实无法推翻,名义上也不能做一丝一毫的让步。
孔子有一个著名的主张,认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正名”。
学生子路认为老师的观点太迂腐,这就引出了孔子的那段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正是因为儒家把名分问题摆在了政治学的制高点,所以儒家才有一个别称,叫作名教,那些扰乱名分规则的人因此被称为“名教罪人”。
这种价值观确实很有迂腐的一面,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比虚无缥缈的名分重要得多,后者完全应该为前者让路。
▲资治通鉴残卷实干家往往会有这种态度,最著名的就是曹 *** ,他在位高权重的时候饱受猜忌,有舆论要他交出兵权,回到封国养老,曹 *** 为此写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自己绝不交权,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没有实力来抵挡政敌的迫害了,家族和国家都会遭殃。
说到这里的时候,曹 *** 留给我们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名是虚的,祸是实的,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资治通鉴》是以“稳定”作为核心政治诉求的,在儒家体系里边,必须正名才有稳定。
所以,司马光才会以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这么一个“名不正”的小事件作为开端,将这个表面上的小事件解读为全部历史当中最大的教训。
因为《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编写的史书,而不是史官编写的史书,“资治”二字是重点。
《资治通鉴》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历史哲学专著。
《资治通鉴》作为历史哲学专著,一开篇就要确立一套价值体系,标榜出这套价值体系里的核心诉求。
全书从哪一年开始,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开宗明义之功的古代意识形态问题。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由政治家 *** 刀,意图在于“资治”的编年史,一开篇就让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主角,开宗明义地讲出一个国家最应该有的核心诉求:稳定。
《资治通鉴》之前的一切正史,从《史记》、《汉书》到《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没做到这一点。
史官写的历史和政治家写的历史,就是如此不同。
借用莎士比亚的台词:在《资治通鉴》面前,“此前所著,皆为序章”。
从编年史的技术角度来看,《资治通鉴》是接着《春秋》和《左传》来写的。
《春秋》站在鲁国的角度,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开始,结束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这是孔子去世的时间。
《左传》作为《春秋》的补充读物,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交代了鲁哀公的人生结局,还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中原强国晋国以智襄子为主帅,进攻郑国,郑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以陈成子为主帅,出兵援救郑国。
陈成子对智襄子有一句评价,原话是“多陵人者皆不在”,意思是经常欺负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左传》有一种叙事风格,凡是这种评价性质的,带有预言意味的话,后文都会出现相应的事实,以此证明前边的评价很恰当,预言很准确。
既然记录了陈成子这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后文就要交代这句名言是如何应验的。
所以《左传》虽然编年结束在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但在全书的最后,宕开一笔,跨越多年,记载智襄子因为贪得无厌和刚愎自用的缘故,被晋国的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灭掉,这才结束全书。
《资治通鉴》编年的开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发生的历史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从此才有了战国七雄当中的韩、赵、魏三大强国。
《资治通鉴》虽然详细记载了智襄子身死族灭的前因后果,明显接上了《左传》,但从严格的编年意义上看,《左传》编年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距离《资治通鉴》开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早了足足65年;《左传》记事结束于智襄子身死族灭,这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距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也还有整整50年。
如果《资治通鉴》真想续接《左传》,为什么要留出这么大的一段编年空当呢?名分和事实,哪一个更重要?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来看,智襄子的灭族,有一场春秋战国时代罕见的大规模战役,堪比长平之战,当然值得大书特书,而周威烈王把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封为诸侯,只不过是一纸任命,波澜不惊。
再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两件事明显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前者骇人听闻,后者水到渠成。
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消灭智襄子,瓜分了智氏家族的土地、财富,“三家分晋”局面已成,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件事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然而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的意义远不如周威烈王的分封来得重要,前者只配作为后者的补充说明,不配作为一部历史哲学著作的开篇。
这样的斟酌和取舍,显示出政治家的历史观和史学家的历史观截然不同。
在政治家看来,一件表面上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事情,其实涵义重大,影响深远,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以儒家的标准来看,“三家分晋”属于礼崩乐坏的典型事件,韩、赵、魏和智氏家族这四大家族都是晋国的贵族,却完全无视晋国国君的存在,自作主张掀起内斗。
而在司马光看来,所谓“三家分晋”只是三大家族“事实上”瓜分了晋国,形成了三个独立政权,而若干年后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意味着三家作为三个新兴的独立政权,从此拥有了合法的名分,在“名义上”可以和晋国国君分庭抗礼。
也就是说,原本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竟然获得了官方认可,把自己洗白了。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名义问题是底线问题,哪怕既成事实无法推翻,名义上也不能做一丝一毫的让步。
孔子有一个著名的主张,认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正名”。
学生子路认为老师的观点太迂腐,这就引出了孔子的那段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正是因为儒家把名分问题摆在了政治学的制高点,所以儒家才有一个别称,叫作名教,那些扰乱名分规则的人因此被称为“名教罪人”。
这种价值观确实很有迂腐的一面,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比虚无缥缈的名分重要得多,后者完全应该为前者让路。
实干家往往会有这种态度,最著名的就是曹 *** ,他在位高权重的时候饱受猜忌,有舆论要他交出兵权,回到封国养老,曹 *** 为此写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自己绝不交权,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没有实力来抵挡政敌的迫害了,家族和国家都会遭殃。
说到这里的时候,曹 *** 留给我们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名是虚的,祸是实的,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资治通鉴》是以“稳定”作为核心政治诉求的,在儒家体系里边,必须正名才有稳定。
所以,司马光才会以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作为开端。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