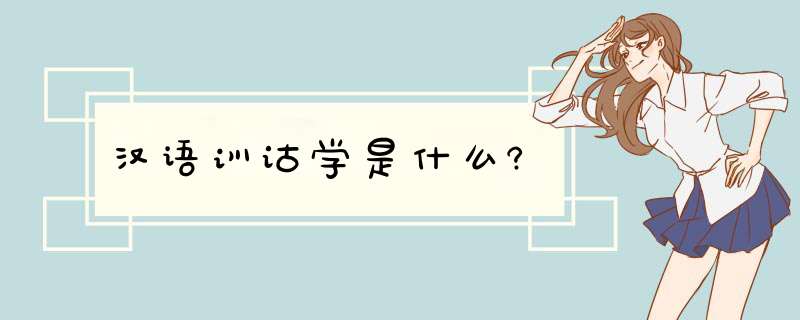
[拼音]:Hanyu xunguxue
中国语言文字学中一门传统的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科。“训”是说明解释的意思,“诂”本义是古言的意思,引申也作解说古语讲。“训诂”的原意是用通行的语言解释不易为人所懂的古字古义,目的在于疏通古书的文义,讲明字义。后来就作为解释词语音义的泛称。
“训诂 ” 一词在班固《汉书》里多写为“训故”。“故”就是古语。如《刘歆传》说:“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又《扬雄传》说:“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训故”与“训诂”同义。章句是分章析句,解释一章一句的意思,训诂是专指讲明文字的音义,两者不相同。训诂学就是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问。旧日只看作是“小学”的一个部门,现在正逐渐发展为一门有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
语言里的词因时代有变迁,而有古今之异,因地域有不同,而有方言之别。因此,后代的人读古代的著作不能懂,就要以今语释古语;同一事物,不同的方域称名或有不同,就要用通语释方言。语言总是在发展的,语词在使用中意义也常常会有改变。一个词由一个意义引申发展出别的意义,就成为一个多义词。多义词在使用时场合不同,意义就不一样。为免去误解,也往往需要加解释。这些就是训诂所由起。久而久之,就有集中讲解字义词义的书,这种书就称为训诂书。语言的各个方面都是有系统的。语音的声韵有系统,词汇的构词有系统,词的音与义和词与词的音与义之间的关系也是有条理可寻的。因此由一字一词的解释进而有意识地从事联贯的、有系统的语义研究工作,创造出科学的理论,对汉语发展历史的理解,对解释古书,对编纂字典、词典,对语文教育都会有重要的贡献。
训诂学的内容和任务训诂学既然是研究词义的学问,其研究的对象主体即是古代的书面上的语言材料,而现代方言的口语资料也在参考之列。要研究古代的书面语,应当具备文字、词汇、语法以及语音史的基本学识,掌握语言文字一般的发展规律,才能从事整理研究前代的训诂资料,总结前人研究词义的理论和方法,并进一步开创新的途径,作深入广泛的研究。
前代解释语词的资料极为丰富,研究工作者应当按照时代的先后,按照不同的性质,分别层次加以整理。前代的训诂学家解释语词时所应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训诂学上有所谓形训、义训、声训。形训是就字形本身的结构说明所表现的词义的。义训是用现代人所理解的词语解释字在书面上使用的含义。采用一个同义或义近的词或一句话作解释。声训也称音训,是从词的读音上着眼,使用音义相通的词来说明词义,或有意识地从音上探求词义的来源。三者之中,义训用的最为广泛,不过如何加义训也是随词而异的。要研究前代的训诂,对古代的训诂书、字书、音义书以及韵书中怎样解释单词,怎样解释固定的词组和联绵词,怎样就文意说明词的通用和假借以及字音改变而意义不同之类的问题,都需要从事分门别类整理,求出通则,评定是非,从中吸取符合语言实际的有用的经验。
进而言之,凡是一门学术必然有理论、有方法。前代许多研究训诂的专家在解释词义的实践中曾提出很多重要的见解。如词与词之间音义相比的关系,通语与方言同实异名的关系,谐声字声符与字义的关系,本义与引申义和假借义的关系等等。在理论上就有所谓右文说,字义起于字音说,音同义近说,一声之转说,古假借必同部说。同时还提出探求词义的一些主要的方法。如形、音、义三者互求,因声以求义,比例文辞以相证,“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戴震《转语二十章序》)等等。这些都是从研究《诗》、《书》古训而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缘由。今日在总结继承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语言研究工作者就要根据现代语言学的原理,研究词义的引申和由旧词派生新词的规律以及正确解释词义的方法;还要研究辨别同义词的法则,词义与语法的关系以及修辞对词义的影响等问题,从而建立起科学的汉语语义学。
训诂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汉语历史久远,有文字的记载已经有4000多年,而语言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有变化。春秋战国以前,一个字大都是一个词。春秋战国以后,构词法有了发展,双音词逐渐多起来,字在增加,字义也有引申和变迁。想要了解古书中的词义不能不有解释。因此在先秦书里就有不少解说字义的材料。其中有据字形说义的, 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说: “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说:“故文,反正为乏”;昭公元年说:“于文,皿虫为蛊”。有从字音推求字义的,如《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与“养”,“校”与“教”,“序”与“射”都音韵相近。在《易经》里,如《说卦》说:“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都从音立训,也属同一类。又有用同义字来作讲解的,如《易经·杂卦》说:“恒,久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这些都是字的常用义。有些字所代表的概念比较难懂,或别有专指,就采用语句加以说明。如《易经·系辞下》说: “幾者动之微, 吉凶之先见者也。”《说卦》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孟子·梁惠王下》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一一分别说明,力求明确,免有疑惑。在战国时代,“名家”是一时的显学,辨析名实,尤为精密。如《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中,同长也”,“圜,一中同长也”,“信,言合於意也”,“间,不及旁也”,“盈,莫不有也”,“梦,卧而以为然也”。这些可以说近似科学的定义了。
周代自平王东迁雒邑以后,王室的势力日趋衰弱,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人民转徙不安,语言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变化。北方黄河流域有了区域共同语,凡是古语或方言为人所不能理解的就要用当时通行的语言即所谓“雅言”来解释。《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中夏”之言。《孟子·梁惠王下》解释齐景公时命太师作乐,诗云“畜君何尤”一句说:“畜君者,好君也。”又《滕文公下》解《书经·大禹谟》“洚水警余”句说:“洚水者,洪水也。”又《左传》宣公四年说:“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这些又是以通语解释方言的例子。由以上所说可以充分理解训诂之兴在春秋战国时代。
训诂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约有4种原因:
(1)语言有发展,古今语有不同和方言有不同;
(2)书面语用词与当时口语用词有不同;
(3)社会不断发展,名物繁多,一词多义的现象比较普遍;
(4)对用词表达思想的作用的理解和认识有了提高,逻辑思维日趋严密。因为有了以上几种原因,所以训诂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很好的开端。
两汉的训诂书与经传的注释汉代是训诂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秦末社会的动荡,语言起了很大变化,先秦古籍多凭口耳传受,用隶书写出,世称为“今文经”。而从汉武帝以后前代的“古文经”出现日多,其中多古字古义,不尽为人所识,因此就有训诂学家为之注释。但在西汉时期, 今文经盛行时, 注释五经的人已经很多。以《诗经》而论,就有齐、鲁、韩三家,文字颇有不同。其他各经也有章句训释之类。汉代的训诂学就是依靠经学而发展起来的,而且汉代已有专门解释词语的训诂书。主要的训诂书有《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4种。这4种书各有特点,是中国训诂学的基石。
《尔雅》是由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训诂书,无作者主名,从内容看应当是战国至秦汉之间经学家和小学家迭相增益而成的。旧说是周公所作,或说是孔子门人所作,都不足信。《汉书·艺文志》著录为3卷,20篇,今存19篇。书中《释诂》、《释言》、《释训》3篇是解释名物以外的语词,其余16篇是解释各种事物名称的,如亲属、宫室、器物、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之类。书中所释的词语主要是出自经传古籍。“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尔雅”就是言辞近于雅正的意思。书中有的以汉代的今语释古语,有的以雅言释方言,有的以俗语释雅言。《释诂》、《释言》、《释训》3篇主要是类聚一般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用一个通用词作解释,如《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其他各篇主要是类聚同类事物的名称分别解释。有古今称名不同的,有异名同实的,有同名异实的、用单词不能解释的,就用一句两句话作解释。品物多方,训解的方法也有不同。这是汉代早期一部训诂的总汇,成为后代解词释义的重要根据。汉代的训诂学也就由此开始发展起来(见《尔雅》)。
《尔雅》之后,西汉末扬雄作《方言》,东汉和帝时许慎作《说文解字》,东汉末刘熙作《释名》,都是极为重要的著作。
《方言》的全称是《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中有绝代语释和别国方言。《 隋书·经籍志 》题为《方言》。扬雄,蜀郡成都人。汉成帝时到长安为郎,他由从四方来到长安的孝廉、卫卒的口里调查殊方异语,条列排比,整理成书。原书为15卷,今存13篇。这是专门解释方言语词的一部著作,所解释的语词有的是古代的方言,有的是当时不同区域的方言,把意义相近的列为一条,用当时通用的同义词作解释,并分别说明不同语词所通行的地区。这不仅是一部重要的训诂书,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方言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很高的价值(见《方言》)。
继《尔雅》、《方言》之后出现的《说文解字》为东汉和帝时许慎所作,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按照字形偏旁分部编排的字典,虽是一部字书,也是一部训诂书。许慎是贾逵(公元30~101)的学生,精通五经,既通今文经,也通古文经。他在《说文解字》里利用不同方式解说字义。有根据字形的构造说明造字的本义的:如“理”, 治玉也;“忘”,不识也;“须”,面毛也;“突”,犬从穴中暂出也;“炙”,炮肉也。有根据古训以说明常用的词义的:如“慈”,爱也;“劲”,彊也;“ 辟”,法也。其中有许多是字的古义:如“沫”,洒面也;“ 浴”, 洒身也;“澡”,洒手也;“洗”,洒足也;“ 颂 ”,貌也(同容);“翁”,颈毛也;“奭”,盛也;“爱”,行貌;“”,丹砂所化为水银也(即“汞”)。书中也有从声音上来作解释的:如“诗 ” ,志也;“尾”,微也;“马”,怒也,武也;“夜”,舍也,天下休舍也;“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也。还有从字的声旁说词义的:如“斐”,分别文也;“贫”, 财分少也。又有根据方言为训的:如“夥”,齐谓多为夥;“眮”,吴楚谓瞋目顾视曰眮。《说文》解释一个字从形音义三方面着想,立意精深,对后代的字书、训诂书影响极大(见《说文解字》)。
《释名》又是另外一种训诂书,作者刘熙专从词的声音上推求事物所以得名的由来,用同音或声韵相近的语词作解释。这种方法训诂学上称之为“声训”,或称之为“音训”。声训本起于战国末,西汉时今文经家多从声音上解说字义,刘熙是要从语言出发来研究事物命名所以之故,跟今文经家不同。他是有意识地要把语音和语义联系起来,就音以求义。例如《释名·释天》说:“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虽然不免有主观唯心成分。但是从声音上推求各种事物名称的取义,类似寻求语源,对训诂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见《释名》)。
汉代的训诂书还有《小尔雅》、《通俗文》。总起来说,各种解释词义的方法在汉代已经具备。最著名的训诂学家大部分都是古文经家。东汉时期古文经盛行,如贾逵、马融(公元79~166)、服虔、郑玄都先后注解经传。郑玄,兼通今古文经,所注最多。他能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以发疑正读,成为“汉学”的正宗,与许慎并称为“许郑”。
魏晋南北朝训诂义疏之学在魏晋时期,张揖和郭璞是最著名的训诂学家。张揖是三国时魏明帝太和年间的博士,他搜罗汉代以前古书的词语和相传的古训纂集为《广雅》一书,体例完全依照《尔雅》,而补充《尔雅》所不备,所以名为《广雅》。张揖又作《古今字诂》和《难字》,见于《隋书·经籍志》,今已失传。郭璞是东晋河东人,为弘农太守著作郎,博学多识,精通训诂,所作古书注释最重要的有《尔雅注》和《方言注》。《尔雅》在汉代已有好几家注本,郭璞别为新注,超越前人所作,他既能以今语释古语,又能以方言释雅言,诠释品物的形貌,以及其功用等尤为明晰(见《尔雅》)。他所作的《方言注》能贯通古今,以晋代方言解释古代方言,并且联系语音,提出音有通转,为训诂研究增添了新的方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人民播迁流转,语言起了很大变化,古书词义艰深,不易理解,于是注释古书的风气日盛。魏晋时期,不仅《易》、《书》、《诗》、《左传》、《穀梁》、《论语》等儒家经典有注,其他古书如《史记》、《汉书》、《老子》、《庄子》以及辞赋之类也有人注释,训诂之学得以不致废坠。其中精义颇多,不无可取。自宋齐以后,兼释经注的“义疏”体出现,如梁代国子助教皇侃著有《礼记义疏》、《论语义疏》。义疏的兴起可能是受了佛教经典有“讲疏”的影响。
魏晋以后除经传有注释外,字书和辞书都多起来。字书和辞书之增多与语言词汇的范围扩大,文字的增多和一词多义有直接的关系。晋代有任城吕忱作《字林》7卷,仿照《说文解字》而有所增益。宋代何承天有《纂文》3卷,北魏阳承庆有《字统》21卷。梁代阮孝绪有《文字集略》6卷,顾野王有《玉篇》30卷。现在所存只有唐人增字本宋修《大广益会玉篇》。顾野王原书只有5卷残卷。其他各书清人都有辑佚本。
隋唐时期的训诂学隋唐时期承接魏晋南北朝注释古书的风气纂著更多。隋代陆善经有《昭明文选注》,唐代李善也有《文选注》。孔颖达(574~648)奉诏作《五经正义》,包括《毛诗》、《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左氏传》。同时又有贾公彦作《周礼注疏》,徐彦作《春秋公羊传注疏》,杨士勋作《春秋穀梁传注疏》。这些书都是参照前代已有的注释而有所抉择。李善书除解释文词字义外,并注明字音和字的通借,对文句的出典尤为注意,成为一种注释的体式。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不仅解释经文,而且解释注文,对语言中的虚词和文法也有不少的解说,这是以前古书注释中少见的。
在经部集部以外,子部、史部书籍也有注释。如杨倞有《荀子注》,成玄英有《南华真经义疏》,司马贞有《史记索隐》,张守节有《史记正义》,颜师古有《汉书注》,章怀太子李贤有《后汉书注》,这都代表了一时的风气。虽然是随文释义,但是也汇集了许多前代的训诂资料。
隋唐时期,韵书盛行,可是字书也不少。如隋代诸葛颖的《桂苑珠丛》100卷,唐武则天的《字海》100卷,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30卷,卷帙都极繁富,应有可观。可惜久已亡佚无存。但就前代书中所引到的材料来看,解词释义已改变旧观,由笼统而趋向于清晰,同时也由只记书面常训进一步注出当时口语使用的意义。这确是一种新的改变。就解词的范围而论,既有专门解释双音词的书(如《兼名苑》),又有专门解释日常应用的口语词的书。现在还能见到的有出自敦煌石窟的《字宝碎金》和《俗务要名林》,都是极珍贵的材料。
唐代在字书、韵书以外还有一类音义书。音义书一类始自魏晋,主要为经部书注音。到陆德明纂集前代各家所作书音(经书外,包括老子、庄子、孝经、论语、尔雅)为《经典释文》30卷,注音之外,有时涉及字义。到北齐时曾有沙门为佛典作音义。后至唐代高宗时释玄应作《大唐众经音义》(通称《一切经音义》(玄应)),唐宪宗时释慧琳又根据玄应书扩充,作《一切经音义》(慧琳)。这两部书都仿照《经典释文》的体例,就原本经文摘字为训,所采古代训诂资料极多,而且有所辨析,在传统小学书中独为一类,对研究前代训诂极为有益,所以随着藏经一直流传下来。清代学者从中辑录出许多训诂材料。
宋元明时代的字义研究宋代承接五代时期研究古文奇字的风气,学者对大量出土的钟鼎彝器广事搜罗,扩大了眼界,学术思想也因之大为解放。在经学方面已不完全斤斤墨守古人的成说,而别创新义,如欧阳修的《诗本义》,王质的《诗总闻》都是如此。在解说文字方面则出现了王安石(1021~1086)的《字说》。王安石《字说》把形声字都说成是会意字,“六书”缺而为五,如谓“与邑交”为“郊”,“同田”为“富”,“讼者言冤於公”之类,完全出于主观臆断,虽行于一时,终不免为人所弃置不顾。
但同时有另一学者王子韶,他倡“右文说”,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音,而且表义。凡谐声声符相同的字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义。如“戋” 是小的意思。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都以戋为义。汉字的形声字一般是形旁在左,用以表义,声旁在右,用以表音,所以称声旁为右文。王子韶,字圣美,浙右人,有《字解》20卷,失传。他所创声旁有义的学说对后代的训诂学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有很大的启发。
宋代研究《尔雅》的有邢昺(932~1012)、郑樵两家。邢昺有《尔雅疏》,补郭璞注所未详;郑樵有《尔雅注》,引旧书以证郭;都各有发明。在南宋期间,朱熹(1130~1200)是重视训诂的人,他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书。既采用前代旧注的优点,而又参酌新解;解经说字能运用到钟鼎彝器的铭文,见于《诗·大雅》、《行苇》、《既醉》、《江汉》诸篇,这是以前所少见的。
在宋代以前,学者对古今音异是比较模糊的。到南宋时期才开始注意到古韵问题。吴棫作《韵补》,从古代的韵文材料中考察古人分韵与《广韵》的异同,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也提出“诗韵”与后代音不同。郑庠又作《古音辨》,讨论《诗经》分韵的大类。这是清代学者研究古韵的先导。对研究词义有一定的帮助。
元代在字学上承接南宋时期的“六书”之学,并不注意研究训诂,所以在训诂方面除有两三种经传注释外,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明代学术不振,受宋代性理之学的影响,游谈无根。训诂书籍有万历时朱谋所作的《骈雅》,类聚古书中义近的双音词,按《尔雅》体例分类,每条予以解释,所以称为《骈雅》。这是一部属于雅学的书。在万历以后研究古学的风气日盛,如江宁焦竑(1541~1620)、成都杨慎(1488~1559)、桐城方以智(1579~1671)等人都有著述阐发字义。方以智的《通雅》,根据古代的语言材料说明音义相通之理,兼论方言俗语,创见极多,对清代的学者有不少启示。
清代训诂学理论的建立清代学者受晚明焦竑、杨慎等人提倡古学的影响,极力推崇汉代的经学和小学,重考据,求实证,不尚空谈性理之学。到乾嘉时代“汉学”大为昌盛,为经书、子书作注解的人很多。要解释经传就不能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因此语言文字之学盛极一时。《说文》、《尔雅》成为人所必读之书。研究《说文》、《尔雅》的重要著作都多至数十种,或刊正文字,或发明古训,各有述造。其他如《方言》、《释名》、《小尔雅》、《广雅》等书也有人为之疏通证明。训诂之学有了极大的成就。著名的训诂学家指不胜数。
清代训诂学的发展跟古音学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自清初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根据《易经》、《诗经》等书的韵字开始把古韵分之为十部起,经过江永(1681~1762)、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1752~1786)、江有诰等人的研究,逐渐加详,发展为二十二部,同时戴震又提出韵类通转的学说。在声母方面,钱大昕又提出声转的说法,而且发明轻唇音古读重唇音,舌头音、正齿音古归舌头。这些都成为研究先秦古籍和探讨字义的根据。
在理论方面,清代学者在训诂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沟通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研究文字和字义必须理解声音,不理解声音就无以解决从文字形体上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有时会陷于迷惘而不知所措。因为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所以必须了解文字的声音,从声音去探求意义。戴震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六书音均表序》)这是很重要的见解。后来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里说:“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段玉裁为王念孙《广雅疏证》作序,也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这些话十分精辟,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训诂的准绳,从而建立了许多推考字义的理论和方法,把零散的知识贯串起来,使训诂学在中国语言学科中成为有系统、有理论、有严谨方法的一门学问。
清人研究训诂的目的,从实用的意义来说,首先是要解释经传和其他隋唐以前的古书。他们应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从声音上推求文字的假借。古书之所以难读,一是由于有古字古义,二是由于文字上有假借。古字古义当考之《尔雅》、《说文》和其他前代书中的诂训,文字上的假借当求其本字。王念孙说:“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王引之《经义述闻序》)那么,假借与本字的关系首先是音同或音近。段玉裁指出:“假借必取诸同部。”(《六书音均表》“古假借必同部说”)所谓“同部”就是属于古韵的同一部。因此,凭借古韵的知识,按照文字上的同音或音近的关系,再参之以文义来推求本字,就可以解决许多古书中难解的文句和古人所加的训诂上的问题。这是清人研究训诂方面的一大发现。
(2)确定字的本义,根据本义以说明引申义。清人认识到音有古今之异,同时也认识到词义有古义,有今义;有本义,有引申义。如“曾”作为虚词用,古义同于“乃”,后世用为“曾经”的意思。“仅”唐以前作“约近于”的意思用,后世用为“但”的意思。这就是古义与今义之分。又如“荟”,《说文》解为“草多貌”,引申为凡物荟萃之义(《说文》段注)。“过”,《说文》训“度也”,引申为有过之过(段注)。这就是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汉语词汇中一词多义是常见的现象。段玉裁说:“凡字有本义焉,有引申假借之馀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馀义者,其失也固;习其馀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蔽与固皆不可以治经。”(《经韵楼集》卷一“济盈不濡轨”条)他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说明词义的发展,对辨析字义极为重要。
(3)比证文句以考定词义。采用古书中相同的文句互相比证以考定词义,宋代人已经这样做了。在清代尤其重视这种方法。段玉裁注《说文》,刘台拱作《论语骈枝》,都能从实证出发解释古训。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尤其善于利用古书的资料,解决从来没有人解决的问题。例如解《诗经》“终风且暴”,为“既风且暴”;解“邦之司直” 为“主正人过” (《经义述闻》卷五),都是颠扑不破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胜义环生,尤为人所称道。王引之作《经传释词》,专门解释古书的虚词,综合各种古书中的用例参互比证,而得其确解,对研究古代文献有极大的帮助。他的书已经联系到语法的范畴了。后来又有人作了补充。
(4)因声以求义。研究字义从声音上来考察,在清代以前虽然也有人注意到,如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宋代王子韶的《字解》,元代戴侗的《六书故》,明代方以智的《通雅》等,但都不曾进行全面有系统的研究,也没有能总结出具体的规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古音的知识,清人有了先秦古音的知识,在前人成说的启发下进一步提出因声求义的原理,把形、音、义统一起来,因形以知音,由音以求义,为训诂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科学的途径。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首先提出“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示部“禛”字注),进一步又说 “凡同声多同义” (言部“”字注)。如从“农”声的字有厚重义,如浓、、脓,从“辰”声的字多有动义,如振、震、唇。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同从一个声符的字不一定只有一义,而不同声符音同或音近的也可以有同义的关系。段氏指出有这类现象,这就比前人的右文说有了新的认识。王念孙作《 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而又把古书中有关的声近义通的字都联系起来解释,“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着重从语言的角度说明其间的音义相通和声音相转的关系。这种作法接近于词族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王念孙又作《释大》一篇,从声母方面观察声母相同而意义也相近的现象,又是一种新的尝试。与王氏同时的程瑶田作《果蠃转语记》,指出凡物的形状、作用相同或相似的往往用声母相同的词来称谓,但字形不必相同。这又把声近义近的道理阐发无遗了。清代的训诂学到王氏父子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研究的范围不仅是单音词,也注意到双音词;不仅研究实词,还研究虚词,初步进入了语法的范畴,对古书的解释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贡献极大。
清人对于训诂的研究所应用的方法主要是以上几种。他们除了注释古书和疏证古代训诂著作以外,还研究一些古代的钟鼎彝器款识,探讨一些文字的古义。并且做一些古代训诂音义的辑佚工作。如黄奭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 任大椿的《小学钩沉》,顾震福的《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是一些资料书。另外,清人还编纂了不少训诂书,如吴玉搢(1698~1773)的《别雅》,史梦兰(1813~1898)的《叠雅》,夏燮的《拾雅》,洪亮吉(1746~1809)的《比雅》等书。阮元还主编了一部《经籍纂诂》,把古书中所见的每字的训释都编录在一起,检一字,而众义俱在,是一部训诂资料的总汇,极为有用的工具书。在历代书籍当中还有很多方言的记载资料,也有人搜集编录,如杭世骏(1696~1773)有《续方言》2卷,程际盛又有《续方言补正》1卷。程先甲又有《广续方言》。其他方言、俗语也有人集录。如钱大昕有《恒言录》,胡文英有《吴下方言考》,毛奇龄(1623~1716)有《越语肯綮录》,翟灏(1736~1788)有《通俗编》等等,为研究古今方言俗语提供了方便。
清代人研究训诂的成绩是大的,但也不无缺点。主要的缺点有两方面 : 一是在段玉裁以后有些学者墨守《说文》,以为《说文》的字都是本字,《说文》的训解都是本义,一词一语都要到《说文》去寻本字,执碍而难通。不知《说文》9353字中有古字,也有汉代后起的增益偏旁的字,具有前后不同的产生层次,不能作为平面的看待;其训解以通用义为多,也并非都是本字本义,甲骨文、金文的佐证很多。二是讲解训诂,声转无方,凡言“语转”、“一声之转”之类未必合于先秦古音,滥用通转之说,所言多误,如钱绎《方言笺疏》之类,足为先戒。
近代以来训诂学的发展20世纪之初到现代研究训诂的学者继承清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吸收了外国的一些早期的语言学的知识,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字原和语根的探求。章炳麟作《文始》,取《说文》中的 510个独体字和半独体字作为“初文”和“准初文”,推求由同一“初文”而繁衍出来的音义相关的语词。凡音义皆近,叫作孳乳,音近义通,叫作变易。目的在求“语源”,求语词之间的亲属关系。但可惜没有脱离文字形体的束缚,所求不是“语源”,结果是文字之原,他用的方法是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在声音的通转上又以他所定的《成均图》为根据,有些也失之勉强。
其后,沈兼士作《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主张以形声字为出发点,用归纳的方法研究形声字同一声符所表现的基本意义。但同一个声符所表现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一个,也当有所区别。形声字的声符,凡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可以构成一个词族,由此再联系音韵,借重古音的知识(包括声母韵母),以求其语根。以实际证据为主,不以主观想象为断,其结果必较可信。这种理论无疑问是正确的。就研究的方法来说,把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来研究,溯源探委,具有创新的精神,大为学者所重视。他后来所主编的《广韵声系》就是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张本。
(2)研究同源字。同源字是音近义同和义近音同的字,合在一起可以定出是同出一源。类聚同源字的意思也是在寻求语源。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同源字大都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在原始的时候本来是一个词,代表某一基本概念,后来语音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才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但是同义词不都是同源字,要以声音是否相近为定。王力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古代的训诂资料,探微索隐,编成《同源字典》一书,以韵部为纲,声纽为目,条理秩如,是研究汉语词义学的一部新著。
(3)虚词的研究。近代因为语法学的兴起,虚词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最明显的改变是研究虚词的人对虚词的词类和用法都有比较清晰的说明。杨树达曾根据《马氏文通》作《高等国文法》,后来就以《高等国文法》为基础, 参照王引之 《经传释词》,作《词诠》一书。专门解说虚词。其后裴学海又作《古书虚字集释》,集录前人所说,并加以补正,与《词诠》相得益彰。吕叔湘有《文言虚字》一书,简明赅要,是学习古代文言文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4)根据出土的古铜器铭文考订古书的训释。先秦的古书都以篆书古文书写,到汉代经过传写,后来又转写为隶书,文字伪变已多,汉代以来的解释往往有误。现代可以借助商周铜器铭文解决一些前代义训中的症结问题。王国维首先以铜器铭文解释《诗》、《书》中的常用词语(《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别开生面 。后来一些古文字学家继踵而起 ,创获更多。在这方面成就最多的是于省吾。他平生所最服膺的是王念孙,所以他所著的书都重实证,不为凿空之论,如《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等书驳正前人误解的地方极多,为利用古文字资料刊正古书创立出一种新的门径。
(5)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唐宋以后语词的考释。清代学者对一些通常在书面上见到的口语词已经有所集录,大都是随笔札记,略明出处,而解释不多。近代以来,罗振玉虽有《俗说》一书,稍补前人著述所不备,但仍属札记性质,还不能说是训诂的研究。惟到张相作《诗词曲语词汇释》 一书才开始作唐以后诗词曲语词的研究。诗词曲中很多习用的不容易懂的口语词在字书和词书中都没有解释,张相一一举例,比证详考,作出解释,是一种新的成就。同类的著作还有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都有很精到的解释,为阅读唐以后的文学作品提供参考。
训诂研究的展望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肇始于先秦春秋战国时代。训诂之所以兴,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变化。古的语词,后人不懂,就要有解释,方言有歧异,或语词在表义的内涵上赋予了新义,也需要有解释,所以就产生训诂。
从训诂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训诂学的兴盛,两汉是一个高峰,清代是一个高峰。两汉学者的训诂著作和经传的注释为训诂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汉训诂学的兴盛跟语言变化的加剧和古文经的传布有极大的关系。清代的训诂学有理论,有方法,发展为一门语言学科,跟经学、史学的考证和古音学等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学者受语言学、语法学的影响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范围上都有了新的建树,改变了旧日墨守古训,拘牵文字形体,和重古略今的风习,开创了新的途径。
研究训诂对解释古书,了解古代的科学文化和考证语言发展的历史以及校勘古书、编写字典辞书都有重大的作用。今后的训诂学从理论上和实用上都会向建立有科学体系的汉语语义学的方向发展。理论的开拓将给词汇学和词典学提供科学的根据。具体的工作,首先是总结前人的成果,吸取前人研究的经验和外国语义研究方面的理论,联系古今,旁及方言,分别层序,研究词义发展的各种现象,并寻出一般的规律,给语文教学和编纂词典以帮助。还有根据古今不同时代的语音系统,从音与义的关联上从事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词族的研究,这项工作的完成将为汉语发展史增添新的重要内容。
- 参考书目
-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韵楼原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郝懿行:《尔雅义疏》,家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王念孙:《广雅疏证》,家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南京,1985。王引之:《经义述闻》,家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南京,1985。黄侃:《训诂述略》,载《制言》杂志, 1935,第7期。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洪诚:《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4。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